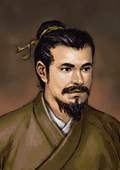
裴松之
字號(hào):字世期
生卒:372—451
朝代:南朝宋
籍貫:河?xùn)|聞喜(今山西聞喜)人
簡(jiǎn)評(píng):史學(xué)家
生平簡(jiǎn)介
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shí)已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后博覽典籍,學(xué)識(shí)日進(jìn)。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shí)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dān)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fēng)險(xiǎn)過大,遲遲不肯動(dòng)身。不久,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chǎng)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后擔(dān)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后升調(diào)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shí)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shí)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zhuǎn)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后,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tuán)中的重要成員。
南朝宋代晉以后,裴松之歷任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冗從仆射等職。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遣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歸來,他將所探詢的吏政民情,歸納為二十四項(xiàng)條款。不久,他被升任為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賜爵西鄉(xiāng)侯。晚年,裴松之先后出仕永嘉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瑯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年),裴松之65歲,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領(lǐng)國子博士,最后進(jìn)位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因病去世,終年80歲。
裴松之的著作,除了著名的《三國志注》外,還有《晉紀(jì)》。另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記載,還有《裴氏家傳》四卷、《集注喪服經(jīng)傳》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此外,《文苑英華》卷七五四,又講他還寫過《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
主要著述
裴松之在東晉時(shí)歷仕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jiǎn),命他為之作補(bǔ)注。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shí)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wù)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yuǎn),而事關(guān)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cuò),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bǔ)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shí)事當(dāng)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補(bǔ)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cuò)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jìn)來,以備參考。對(duì)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píng)論;對(duì)于陳壽議論的不當(dāng),裴注也加以批評(píng)。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shí)期的原始材料達(dá)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jǐn)?shù)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jù)沈家本統(tǒng)計(jì),注中引書“經(jīng)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shí)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yùn)用傳統(tǒng)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yīng)劭之注《漢書》,考究訓(xùn)詁,引證故實(shí)。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xùn)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裴注為史書注釋開辟了新的廣闊道路。但裴松之的注解也有謬誤之處,凡治三國史學(xué)者都熟知,裴松之注雖然可以作為陳壽《三國志》的補(bǔ)充,然其收集的稗官野史,當(dāng)中的訛謬乖違之處不可盡信。
?
為其他書籍的補(bǔ)注
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史書“疏略寡要”、“時(shí)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bǔ)闕列為第一項(xiàng),主要補(bǔ)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jì)》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gè)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rèn)識(shí)與領(lǐng)導(dǎo),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píng)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lǐng)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jìn)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bǔ)充200多字,其識(shí)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xué)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bǔ)其生平與學(xué)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shí)人的評(píng)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jù)。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bǔ)充其生平與重大發(fā)明創(chuàng)造,有關(guān)指南車、翻車、連弩、發(fā)石車以及織綾機(jī)的記載,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的科技生產(chǎn)水平,填補(bǔ)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guān)的重要文獻(xiàn)亦是補(bǔ)闕的內(nèi)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zhì)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備異與懲妄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duì)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jié)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rèn)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于注中,可為備異;又對(duì)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dāng)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jié)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duì)比對(duì)象,再擴(kuò)及到對(duì)其他史書的品評(píng)和總結(jié)。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jù)《春秋》之義,認(rèn)定《魏書》“崇飾虛文”,并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shí)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duì)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于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píng)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xiàn)。論辨包括評(píng)史事與評(píng)史書兩個(gè)方面,評(píng)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rèn)識(shí)的直接表達(dá),因與本論題關(guān)系不大,故略而不論,評(píng)論史書,則有總結(jié)同期史著優(yōu)劣的史學(xué)批評(píng)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nèi)容之一。裴氏對(duì)《三國志》一書的評(píng)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píng)價(jià),又有散見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píng),是較為全面的;對(duì)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píng)點(diǎn),概括來看,這些評(píng)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gè)方面。
主要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
我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后,編年、紀(jì)傳兩體漸趨成熟,盡管仍存在二體優(yōu)劣的爭(zhēng)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guān)注的是對(duì)現(xiàn)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jì)傳體的規(guī)范化問題。紀(jì)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云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余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chuàng)“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后批評(píng)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shí)屬“算無遺略、經(jīng)權(quán)達(dá)變”的奇士,應(yīng)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fēng)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zhì)則異焉”,本質(zhì)的異同,應(yīng)是區(qū)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jì)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jù)“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duì)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于一種自發(fā)狀態(tài)的話,那么,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rèn)識(shí)了。由實(shí)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shí)踐,正是裴注史學(xué)意義在編纂學(xué)上的體現(xiàn)。
在敘事描寫上,強(qiáng)調(diào)通順合理,反對(duì)“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duì)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bǔ)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fēng)藻的時(shí)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xué)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xiàn)了裴氏對(duì)歷史文學(xué)的審美要求,即生動(dòng)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diǎn)同樣具有史學(xué)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