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nbgc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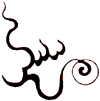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xué)與中晚明士人心態(tài)》 |
|
|
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tài)的流變 本論題是對(duì)陽明心學(xué)與中晚明士人精神生態(tài)關(guān)系的研究。如果就陽明心 學(xué)所發(fā)生的具體原因而言,則是士人們對(duì)明代中期種種變化了的歷史狀況的 回應(yīng),尤其是在明代中期日益險(xiǎn)惡的政治環(huán)境中如何安頓士人個(gè)體生命,更 是其發(fā)生的直接原因。然而,盡管陽明心學(xué)的產(chǎn)生時(shí)間是在弘治、正德年間, 但若從更為深層的原因看,它理應(yīng)是整個(gè)明代前期歷史發(fā)展演變的必然結(jié)果。 陽明心學(xué)猶如一棵大樹,它固然生長于明代中期,但它的根卻伸向了整個(gè)明 朝一代。如果對(duì)明代各種政治文化措施一片茫然,如果對(duì)明代前期的歷史狀 況不甚了了,便很難弄明白陽明心學(xué)發(fā)生的真正原因,也很難把握其學(xué)說的 真實(shí)內(nèi)涵,當(dāng)然也就談不上對(duì)中晚明士人的人格心態(tài)所造成的真正影響作出 準(zhǔn)確的描述了。因此,本章即先從明代前期的歷史狀況談起,以便具體探討 陽明心學(xué)所產(chǎn)生的真實(shí)契機(jī),并為全書的行文建構(gòu)一個(gè)較為寬廣的文化視野。 本章共分三節(jié):第一節(jié)是對(duì)明前期政治變遷中所顯示的皇權(quán)與文官集團(tuán)之間 的關(guān)系,以及在此種關(guān)系中所形成的士人心態(tài)的研究與描述,其核心在于表 現(xiàn)明前期歷次重大政治事件對(duì)士人心態(tài)所造成的影響。第二節(jié)是對(duì)明代文官 銓選制度的研究,其中包括八股制藝的選拔方式與程朱理學(xué)的選拔標(biāo)準(zhǔn)兩個(gè) 側(cè)面,其核心在于探討科舉制度所具有的謀取個(gè)體利益的實(shí)質(zhì)與理學(xué)道德理 想化標(biāo)準(zhǔn)之間的悖離,以及對(duì)士人的人格心態(tài)所造成的負(fù)面影響。第三節(jié)是 對(duì)陳獻(xiàn)章的心學(xué)內(nèi)涵及其人格心態(tài)的研究,其核心在于指出明代思想界試圖 通過心學(xué)的建立來對(duì)時(shí)代進(jìn)行回應(yīng),從而為士人的生命安頓尋覓到一條有效 的途徑,顯示了陽明心學(xué)產(chǎn)生時(shí)那種呼之欲出的必然趨勢(shì)。 第一節(jié):道與勢(shì)之糾纏:明代士人境遇的尷尬 一、方孝孺之死——士人的悲劇與尷尬命運(yùn)的序曲 明代在中國歷史上是個(gè)獨(dú)具品格的朝代。一方面,它像宋代一樣,所采 用的是典型的文官制度。這主要是指其立國的宗旨為禮法并舉的儒家禮樂制 度,其選拔官員的方式為程序嚴(yán)格的科舉制度,其官員構(gòu)成與權(quán)力的實(shí)際操 作也都有受過儒家詩書教育的士人來承擔(dān),更重要的是,士人是這個(gè)朝代實(shí) 際利益的真正獲得者。然而另一方面,明代又是一個(gè)帝王專制空前強(qiáng)化的時(shí) 代。在明初的洪武時(shí)期,朱元璋將中國歷史上曾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的宰相制 度徹底廢棄,把權(quán)力下分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負(fù)責(zé)。至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 設(shè)內(nèi)閣,立大學(xué)士數(shù)名以備顧問并負(fù)責(zé)處理章奏誥敕等文字工作。由此,貫 穿明代二百余年的內(nèi)閣制正式形成。在此種制度下,皇帝的權(quán)力凌架于文官 集團(tuán)之上而缺乏必要的限制是不言而喻的。就理想狀態(tài)言,皇上與文官在共 同遵守仁義禮智的倫理原則亦即儒道的前提下,方能和衷共濟(jì)以求取共同的 利益。如果說皇上代表權(quán)力之勢(shì)而文官集團(tuán)代表倫理之道的話,就需要達(dá)到 勢(shì)以道為依據(jù)而道借勢(shì)以流行的和諧一致。但是由于皇上的權(quán)力與欲望在明 代得不到制度上的限制,因而上述所言的理想狀態(tài)在歷史的實(shí)際發(fā)展過程中 便很少能夠得以實(shí)現(xiàn)。許多士人為此進(jìn)行過抗?fàn)帲踔粮冻隽搜拇鷥r(jià)。于 是在明代前期就形成了一種士人人格心態(tài)由悲憤尷尬趨于疲軟平和的歷史態(tài) 勢(shì)。此一趨勢(shì)的奠基者就是那位死得凄慘而又悲壯的方孝孺。 明人李贄曾對(duì)明前期數(shù)位帝王的施政特征作過一個(gè)概述:“唯我圣祖, 起自濠城,以及繼位,前后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無一時(shí)而不 思得賢之輔。蓋自其托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于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 心之矣。……自是而后,建文繼之純用恩,而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并 著而不謬。仁宗之純用仁,而宣宗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并用而不失。” (《續(xù)藏書》卷一)倘若將此段文字作一簡化,則為:太祖——用威,建文 ——用仁,太宗——恩威并用,仁宗——用仁,宣宗——仁義并用。本段文 字如果剔除當(dāng)朝人對(duì)列祖列宗的崇拜與歌頌的情緒,其論斷則基本符合歷史 實(shí)際。在洪武時(shí)期,朱元璋為矯元末貪污放縱之習(xí),以酷刑整頓吏治,行嚴(yán) 法扭轉(zhuǎn)士風(fēng)。當(dāng)時(shí)的著名詩人高啟、張羽、楊基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連 開國功臣宋濂、劉基也最終郁郁而死,正如解縉在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說: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shí)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明史》 卷一四七《解縉傳》)這是一個(gè)政治穩(wěn)定的時(shí)代,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令人窒息的 時(shí)代,生活在此一時(shí)代的士人,他們所擁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禍避害心 理,而不可能有扭轉(zhuǎn)乾坤的守道抗勢(shì)壯志。只有當(dāng)洪武時(shí)代結(jié)束而朱允炆登 基后,士人們似乎才迎來了轉(zhuǎn)機(jī)。從改元“建文”的新年號(hào)里,就不難發(fā)現(xiàn) 這位自幼飽受儒學(xué)熏陶的年輕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這意味著一個(gè)仁治時(shí) 代的到來。方孝孺則是這仁治舞臺(tái)上協(xié)助建文皇帝的主要角色。 方孝孺(公元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他象洪武時(shí) 的其他士人一樣,亦曾有過痛苦的經(jīng)歷。他生于元至正十七年,明王朝建立 時(shí),已經(jīng)十二歲,元末群雄混戰(zhàn)、生靈涂炭的情景應(yīng)該依稀留在他的記憶中。 其父方克勤曾坐“空印”案而被誅,據(jù)《明史》本傳記載,他曾“扶喪歸葬, 哀動(dòng)行路。”(卷一四一)其本人亦曾被仇家牽連而逮至京師。但或許由于 他太年輕,太祖朱元璋竟然放過了他,認(rèn)為“今非用孝孺時(shí),”而令其處下 僚以“老其才”。這些經(jīng)歷使他具有了特殊的人格心態(tài),四庫館臣評(píng)價(jià)他說: “孝孺學(xué)術(shù)純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于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 于駕軼漢唐,銳復(fù)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fā)揚(yáng)蹈厲,時(shí)露于筆墨之間, 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fā)之。”(《四庫全 書總目》卷一七 0,集部,別集類二三)由此可知孝孺是位學(xué)術(shù)純正而又志 氣豪邁的儒者,他既沒有劉基嘆老嗟卑的畏懼失望心理,也不象高啟那樣缺 乏政治熱情而甘居草野,他不僅自幼“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zhèn)鳌罚┒掖朔N志向是其反復(fù)斟酌、深思熟慮 后的人生選擇。其《立春偶題二首》曰:“萬事悠悠白發(fā)生,強(qiáng)顏閱盡靜中 聲。效忠無計(jì)歸無路,深愧淵明與孔明。”“百念蹉跎總未成,世途深恐誤 平生。中宵擁被依墻坐,默數(shù)鄰雞報(bào)五更。”(《遜志齋集》卷二十四)該 詩顯然作于洪武時(shí)期,在進(jìn)退失據(jù)的情景中,他夜半擁被而坐,默默思考將 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而淵明與孔明這二位退隱自適與濟(jì)世憂民的大賢便是 他此時(shí)的人生楷模。但后來在其所作的《閑居感懷十七首》中,其志向便已 集中于濟(jì)世一端,試選數(shù)首為證:“鳳隨天風(fēng)下,暮息梧桐枝。群鴟得腐鼠, 笑汝長苦饑。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其 二)“乘時(shí)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賢豪志大業(yè), 舉措流俗驚。循循刀筆間,固足為公卿。”(其三)“我非今世人,空懷今 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為秦,周公以為周。哀哉萬年后, 誰為斯民謀”。(其八)(同上卷二十四)依然是身處下僚,依然是境遇窘 迫,卻已經(jīng)自視為鳳凰賢豪,蔑視庸人般的鴟鳥追逐腐鼠,不愿做蕭曹般的 刀筆俗吏,甚至連商鞅、周公的只為一姓一朝亦不被其欣賞,他所追求的是 大禹治水般的忘我奉獻(xiàn)精神,目的是“為斯民謀。”懷抱如此志向的方孝孺, 終于在年輕皇帝朱允炆那里尋找到了實(shí)現(xiàn)理想的機(jī)遇。 建文皇帝登基后即詔行寬政并銳意復(fù)古,方孝孺從中當(dāng)然起了不可低估 的作用。后人對(duì)建文君臣恢復(fù)井田舊制與《周禮》之古舊官稱往往持批評(píng)態(tài) 度,如清人評(píng)曰:“圣人之道,與時(shí)偕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 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幾三千年,勢(shì)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 求六宮改制定禮。即使燕王兵不起,其所施設(shè),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執(zhí) 講學(xué)家門戶之見,曲為之諱。”(《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 0,集部,別集 類二三)建文君臣的行為主張自然是幼稚可笑跡近荒唐,然而卻不必懷疑他 們對(duì)政治理想追求的真誠熱情與君臣間關(guān)系的融洽和諧。方孝孺的所作所為, 完全是對(duì)自己志向的追求與人生理想的滿足,沒有絲毫的被動(dòng)勉強(qiáng)。這種對(duì) 實(shí)現(xiàn)政治理想的渴望與對(duì)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無論從情感還是理念上 都把建文帝視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將自己的命運(yùn)與之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 就此一點(diǎn)而言,在后來的靖難之役中,他是決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就實(shí) 際情形論,方孝孺在所有殉難文臣中,是最有資格也最有可能存活下去的人 物,故后人曾對(duì)此論曰:“惟是燕王篡位之初,齊、黃諸人為所切齒,即委 蛇求活,亦勢(shì)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名聲,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 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jié),可謂貫金 石、動(dòng)天地矣。”(同上)以實(shí)而論,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視為一種個(gè)人的行 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曇花一現(xiàn)后破滅的標(biāo)志。從此一角度言, 可以同意某些學(xué)者的觀點(diǎn),將他的死視為“儒家之絕唱。”①因此,方孝孺 之死的意義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事件本身。現(xiàn)在將《明史·方孝孺?zhèn)鳌分忻枋銎?br> 死的場面摘引如下: 是日孝孺被執(zhí)下獄。先是,成祖發(fā)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 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 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 “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 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 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憂;奸臣得計(jì)兮,謀國用 憂;忠臣發(fā)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憂。” (卷一四一) 或許是為了敘事凝煉的史書體例,本傳省略了一些精彩生動(dòng)的細(xì)節(jié),如 誅滅十族的對(duì)話以及株連八百七十三人的記載等等,但僅此已足以說明問題。 方孝孺的死無疑是轟轟烈烈的,這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他被滅十族的慘烈 結(jié)果,二是那義無反顧的大無畏精神。然而遺憾的是,他面對(duì)的并不是一個(gè) 改朝換代的歷史時(shí)期,而是皇室內(nèi)部的自相殘殺,這使他的以身殉道的壯舉 減少了些許悲壯的色彩,從而帶有某種歷史的尷尬,這從后人的不同評(píng)價(jià)中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明史》評(píng)曰;“忠憤激發(fā),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 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卷一四一)然亦有譏其為迂闊者,王廷相以為 孝孺之死絕難與文天祥相比,他實(shí)為“忠之過者”,因“自激之甚”而卒招 殺身之禍,此種“輕重失宜”之舉措,“圣人豈為之!”(《慎言》卷十三 《魯兩生篇》)至清人吳敬梓作《儒林外史》時(shí),猶借書中人杜慎卿之口評(píng) 曰;“方先生迂而無當(dāng)。天下多少大事,講那皋門、雉門怎么?這人朝服斬 于市,不為冤枉的。”(第二十九回)方孝孺的尷尬源自其兩難:若降順燕 王則有損節(jié)操,若仗義死節(jié)又顯迂闊。 這種尷尬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對(duì)士人操守的影響,這在方孝孺未死之前, 已被姚廣孝所言中,即所謂:“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何以殺孝孺 便會(huì)斷絕天下讀書種子,后來李贄做了明確的解答:“一殺孝孺,則后來讀 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fù)更生乎?”(《續(xù)藏書》卷五)則所謂 讀書種子斷絕,實(shí)在是對(duì)忠義操守的放棄,此乃靖難之役留給明王朝的最大 損失。正是有鑒于此,仁宗繼位后便立即宣布:“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 從寬典。”(鄭曉《文學(xué)博士方公孝孺?zhèn)鳌罚娊垢s《獻(xiàn)征錄》卷二十)但 要挽回已造成的影響顯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其實(shí),此事對(duì)士人節(jié)操的消 極影響當(dāng)時(shí)即已顯露無遺,這從如何對(duì)待周是修殉難的態(tài)度中最足說明問題。 嘉靖時(shí)士人郎瑛在其筆記《七修類稿》中,有“名人無恥”條記曰:“文天 祥在燕京時(shí),欲為黃冠去國,南官王積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qǐng)保釋之,世祖 亦有然意。留夢(mèng)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復(fù)號(hào)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 遂寢其事。我太祖渡江靖難時(shí),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楊士奇、 衡府紀(jì)善周是修同約死節(jié)。明日,惟是修詣國子監(jiān)縊焉。他日士奇為之作傳, 與其子曰:‘向使同尊翁死,此傳何人作也?’嗚呼! 眾固可責(zé)矣,若留、 楊數(shù)言,尤為無恥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尚爾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 (卷十六)無獨(dú)有偶,祝允明《野記》卷二亦記曰:“周紀(jì)善初與胡廣、金 幼孜、解縉、黃淮、楊士奇、胡儼約同死。比難及,周命其子邀諸人,皆不 應(yīng)。周乃獨(dú)縊于應(yīng)天府學(xué)禮殿東廡。”(《國朝典故》卷三二)楊士奇是后 人眼中的名臣,但郎瑛卻將其與無恥之徒留夢(mèng)炎相提并論,似乎有失寬容, 但倘若將此段記載與楊士奇所撰的《周是修傳》相比較,就會(huì)明白郎瑛所言 并非沒有道理,其曰:“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 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廣大、肅用道、楊士奇,且付后 事。暮入應(yīng)天府自經(jīng),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tǒng)。數(shù) 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qǐng)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 無所問。”(焦竑《獻(xiàn)征錄》卷一 0五)觀此知士奇所記與郎瑛相比有兩點(diǎn) 出入:一是將是修與士奇諸人的約同赴難改為“且付后事。”二是有意為朱 棣開脫而頌揚(yáng)其胸懷寬大。這樣做當(dāng)然不能算是信史,但卻既掩飾了自身的 軟弱失節(jié),同時(shí)又討好了當(dāng)今皇上,豈非一舉兩得之舉。當(dāng)時(shí)那些歸順了燕 王的文官們恐怕都抱有與士奇相同的心態(tài),只是未能形之于語言而已。楊士 奇由于遇到了為周是修作傳的麻煩,不得不厚起臉皮來自我解嘲。但這不僅 掩飾不住其內(nèi)心的尷尬,卻適足顯示了其尷尬心態(tài)的存在。鄭曉在斥責(zé)某些 人對(duì)方孝孺的不實(shí)記載時(shí)說:“同時(shí)文學(xué)柄用之臣,際會(huì)功名,史有別書, 以故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曰:后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余生,無乃 非直筆。”(同上卷二十)這樣的評(píng)語移之于楊士奇對(duì)周是修的記載,恐怕 鄭曉是不會(huì)反對(duì)的。當(dāng)然,稱士奇為“無恥”似仍稍顯過分,當(dāng)士人們面臨 或守節(jié)而死或降順而存的嚴(yán)峻抉擇時(shí),理所當(dāng)然地會(huì)有各自不同的作為。以 道德尺度來衡量二者,也許應(yīng)該有褒貶的不同。可是當(dāng)他們面對(duì)明代歷史時(shí), 卻均處于尷尬的境地。在朱氏皇權(quán)面前,他們都顯示了士人的無奈,其區(qū)別 僅僅在于:前者因生命的結(jié)束而失去了守道的能力,后者則主動(dòng)歸順而放棄 了守道的權(quán)力。從士人的精神世界而言,也許后者比前者更為痛苦,前者因 生命的結(jié)束而一了百了,后者卻依然須經(jīng)受無休止的心靈煎熬。當(dāng)人們將目 光轉(zhuǎn)向永樂的士人群體時(shí),便會(huì)發(fā)現(xiàn)上述推斷并不是沒有根據(jù)的。 |
|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版權(quán)所有 北京國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