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nbgc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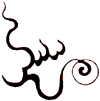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tài)》 |
|
|
第二章王陽明的心學品格與弘治、正德士人心態(tài) 第一節(jié)弘治、正德的士人心態(tài)與陽明心學發(fā)生的心理動機 二、“龍場悟道”的心理動機與王學產生的意義 “龍場悟道”被許多人視為是王陽明學術生涯與生命歷程的轉折點。古 今各家論說甚多,先擇取三家以見一般。陽明本人說:“守仁早歲業(yè)舉,溺 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于眾說之紛繞疲疢,茫無可入,因求 諸佛老,欣然有會于心,以為圣人之學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 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謫官龍場,居夷處困, 動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 江河而放諸海也。”(《王陽明全集》卷三,《傳習錄》下)其好友湛若水則 言其:“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于騎射之習,三溺于辭章之習,四溺于神仙 之習,五溺于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元年)始歸正于圣賢之學。”(同上卷三 八《世德紀》,《陽明先生墓志銘》)黃宗羲亦曰:“先生之學,始泛濫于詞 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于是出 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圣人出此更有何道?忽悟 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 (《明儒學案》卷十)此三人所述應是可信的,故而后世學者將龍場悟道作 為陽明研究的重點,應該說是具有充分理由的。然而亦有持不同觀點者,明 末東林黨魁高攀龍便說:“余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 得養(yǎng)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 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將,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 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于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將之意也。 后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游, 深山夷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灑落。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 學之益精,非于致知之有悟也。”(《高子遺書》卷十)初看高氏對陽明頗不 尊重,且所言與王、湛、黃三人之觀點出入甚大,其實如果仔細辨析,高氏 之言在陽明年譜中均可尋得根據,只是雙方在何者為陽明心學之根基上有分 歧而已。前三人強調了龍場悟道對陽明前期思想的轉變與超越,而后者則更 強調其前期思想對其整個心學思想的基礎作用。高氏的話中顯然有攻擊陽明 心學為異端的意思,但卻不能就此否定其對研究陽明思想的啟示作用。我以 為須將此兩種觀點結合起來,才能理清陽明思想的發(fā)展脈絡,并更加彰顯龍 場悟道的價值意義。 若欲理清陽明前期思想與其龍場悟道之關系,必須首先解決互為相關的 兩個問題,即陽明前期思想有無統(tǒng)緒、若有又以何者為統(tǒng)緒?而欲解決此二 問題,則又須同時弄清陽明當時之人格心態(tài)為何種特征。王陽明(1472— 1528),他本名守仁,字伯安,余姚人。因其曾創(chuàng)辦陽明書院,故世稱陽明 先生。他于弘治十二年中進士,龍場悟道前先后任刑、兵二部主事。他的幼 年曾有不少奇異的傳說,⑤但可信的程度較小,從中充其量只能說明他是個 聰明而有好奇心的孩子而已。能夠看出對其后來的人生發(fā)生了影響的,是成 化十八年他十一歲在京師時的一件事。當時他問塾師“何謂第一等事。”其 師說:“惟讀書登第耳。”他卻疑惑地問:“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 圣賢耳。”(《年譜》一)這固然說明他比一般士子具有更高的追求,但成圣 本是宋代以來理學家常言的志向,且先儒在經書中也屢屢言之,陽明提出如 此志向便不能視為反常之舉動。其幼年所可注意的是,由于優(yōu)越的家庭環(huán)境 與隨其父在京師的廣博閱歷,使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具備了廣泛的興趣。 比如在十五歲時出居庸關了解虜情、觀察地勢與逐胡兒騎射;又于當年聞石 和尚、劉千斤暴動,即向朝廷獻平亂方略;十七歲時在新婚之際入鐵柱宮向 道士扣問養(yǎng)生之說,弄得岳丈家通宵找人等等。對王陽明一生造成了深刻影 響的事件發(fā)生在弘治二年他十八歲時,本年他在攜夫人從江西歸越途中,至 廣信向理學家婁諒問學。一齋先生向他講了宋儒格物之學,但對其精神世界 造成了巨大震撼的卻是“圣人必可學而至”的人生志向。《年譜》說他當時 “遂深契之”,這“深契”的涵意顯然是與其少年的人生興趣發(fā)生了聯(lián)系。 他少年時常常有超越庸常的打算,但究竟如何超越卻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目 標。而如今在婁諒的啟示下,他具有了明確的“學為圣人”的人生目標,不 能不說這對其一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學為圣人”依然是一位青年士人的美好愿望, 至于如何成為圣人以及成為什么樣的圣人,均帶有未定的性質。但有一點是 清楚的,即此時的成圣愿望是緊緊圍繞著陽明成就自我的人生理想而展開 的。這意味著其成圣帶有多種可能性而尚未歸向于一家,而弘治年間的寬松 文化環(huán)境也為他探索成圣的多種途徑提供了條件。如果說陽明前期的思想與 人生追求有什么統(tǒng)緒的話,我以為渴望超越常人的成圣愿望便是其一以貫之 的統(tǒng)緒。至于說他探索的途徑我以為主要有三種:一是循宋儒之舊途,格物 以成圣。自弘治五年至十年,他除了進行科舉考試的準備外,基本把精力用 之于此。可他并沒有取得成功,據《年譜》載,他先是“遍求考亭遺書讀之”, 然后取官署中竹格之,“深思其理不得,遂遇疾。”據說他整整格了七日,可 見其求圣愿望的強烈,而最終歸于失敗的結果,曾對其心靈產生了巨大的震 撼,以致許多年后他依然對此次的失敗感嘆說:“遂相與嘆,圣賢是做不得 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傳習錄》下)二是求實用之學。他在格物失 敗后便改學兵法,于弘治十年“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 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其目的便是成就其“韜略統(tǒng)馭之才”。(《年 譜》一)他對自己的軍事才能及學問是頗為自負的,因而在其中舉后便立即應 詔上“邊務八事”,盡管他條分縷析,講得頭頭是道,而且后來的被任命為兵 部主事或與此有關,卻依然無法以此立下不朽的事功,因為弘治時的明王朝 已不再具有主動出擊的軍事勢力。孝宗亦曾一度有建功邊境的宏愿,卻遭到 大臣們的善意阻止,他問劉大夏:“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大夏曰:“陛 下神武固不下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明史)卷 一八二,《劉大夏傳》)從此孝宗再也沒有萌生過出師的打算,也就意味著陽 明立軍功理想的破滅。三是求養(yǎng)生之說。弘治十一年,“先生自念辭章藝能 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偶聞道士談養(yǎng)生, 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年譜》一)對此事可以存在兩種解釋,未得圣學遂 退而求其次,與認佛老亦為圣學之一種。考諸實際,后者應是正解。這是因 為求養(yǎng)生之學是其龍場悟道前的一貫行為,他不僅有十七歲時向鐵柱宮道士 求學的前期經歷,而且在這之后的弘治十五年歸越養(yǎng)病時,他又一次沉醉于 道教。據《年譜》載:“筑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 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云門,先生即命仆迎之,且歷語其來 跡。仆遇諸途,與語良合。眾驚異,以為得道。”此所言“得道”顯然是成 圣的另一表述,根據后來陽明多次進行圣學與佛老之間同異的辨析,其早年 曾認佛老為圣學應該是成立的。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后,陽明又否定了此種探 索。其原因是醒悟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所謂“簸弄精神”是指玩弄 小聰明而無益于身心之修養(yǎng),而并非是對養(yǎng)生之學的否定,因而便有了“離 世遠去”的念頭,只是由于對親人的思念之情難以割舍,他才最終放棄了出 世的追求。除了上述三種追求之外,陽明還對文學復古發(fā)生過興趣,黃綰《陽 明先生行狀》說:“己未成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 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 文。”(《王陽明全集》卷三八)此處所言有失實之處,如說陽明于弘治十二 年觀政時便與徐禎卿共為古詩文,即甚不通,蓋因徐氏于弘治十八年始中進 士,其與陽明發(fā)生交往則必在正德之后。但陽明曾與前七子有過密切關系并 對詩文創(chuàng)作有濃厚興趣則屬事實。不過他從未將詩文一事置于圣學之位,故 而亦不曾過于貶低詩文,而是始終吟哦不絕。總結上述各點,可以看出王陽 明龍場悟道前在實現成圣的方式選擇上,始終徘徊于儒釋道之間,或者說是 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其核心是對超越凡俗的人生理想的追求。 王陽明的這種思想特征是與弘治朝的時代氛圍密不可分的。這個時代給 了士人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使他們產生了追求理想境界的人生進取精神,而孝 宗的舒緩個性與李東陽們的因循作風又使此種理想的實現變?yōu)椴豢赡堋S谑?br> 新生代的士人便陷入時而亢奮時而灰心的矛盾狀態(tài)之中。王守仁屬于新生 代,他當然也陷入了此種矛盾狀態(tài)。他也象李夢陽那樣有變革政治的雄心, 只不過空同選擇了復古文以復古道的方式,而他則選擇了興圣學以勵士氣的 方式,早在他中進士時所撰的《陳言邊務疏》中,便如此指出:“臣以為今 之大患在于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 交蟠蔽雍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 進言者目為浮躁,沮抑正大之氣,而養(yǎng)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 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王陽明全集》卷九)拿此與李夢陽弘治十八年 《上孝宗皇帝書》所指出的所謂“元氣”之病的思路幾乎如出一轍。事實上, 李、王間關系的密切程度遠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如李夢陽曾記述其在弘治間 彈劾壽寧侯時的情形說:“草具,袖而過邊貢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 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 也。乃出其草視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為若筮可乎?然晦翁 行之矣。’于是出而上馬并行,詣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黃矢吉貞。王曰: ‘行哉!此忠直之由也。’”(《空同先生集》卷三九,《秘錄》)這一方面固 然顯示了陽明的精明機警,但同時也說明他們之間的了解程度之深,而能夠在 一起商議預測禍福,就更非一般泛泛之交可比擬了。正是由于他們的性情相 投,從而決定了他們也必將有著相近的心態(tài)。論參與政治的熱情,陽明決不 比夢陽低,他在弘治十五年所作的《九華山賦》中說:“彼蒼黎之緝緝,固 吾生之同胞;茍顛連之能濟,吾豈靳于一毛!矧狂胡之越獗,王師局而奔勞。 吾寧不欲請長纓于闕下,快平生之郁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于或遭;又 出位以圖遠,將無誚于鷦鷯。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于風泡;亦富貴之奚為, 猶榮蕣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雄杰于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 何避乎群喙之呶呶!”(《王陽明全集》卷十九)他有濟蒼生、滅狂胡的壯志, 卻地位低微,難以展其宏圖。他感到了生命的短暫,更有了時不我待的緊迫 感。但支撐他的整個意識的,是“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的圣人不朽觀念。 不過,他也并非認為只有立功一途可以實現其人生的價值,在兩年之后所作 的《登泰山》詩中,他便表現了另一面的追求:“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 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峰巔,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 斯在。淡泊非虛杳,灑脫無芥蔕。世人聞余言,不笑即吁怪。吾亦不強語, 惟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同上)他本有“匡扶”社稷的大 志,卻被置于可有可無的低位,于是他有了“淡泊”“灑脫”的追求,盡管 可能做不成儒家圣人“魯叟”,卻可以求得自我的適意。此種適意追求當然 不是此時陽明的主要傾向,但也決非一時的心血來潮,在陽明的其他詩作中, 亦曾有過反復的表述:“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后人思。卻懷劉項當年 事,不及山中一局棋。”(同上《題四老圍棋圖》)“謫仙棲隱地,千載尚高 風。云散九峰雨,巖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吊遺蹤。回首蒼茫外,青山 有無中。”(同上《李白祠二首》其二)“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 不如騎 白鹿,東游入蓬島。”(同上《《登泰山五首》其四)塵視劉、項爭霸天下, 神往李白脫俗棲隱,渴望騎鹿仙游,這既是陽明濟世熱情受阻時的憤激情緒發(fā) 泄,也是他自我適意的脫俗情結的自然延續(xù)。但這并非表示他當時果真要采取 棄絕世事的行動,因為此時他不僅依然關心現實政治,而且其追求成圣的舉措 也正從精神的漫游向心學的專一歸攏。弘治十八年是陽明人生歷程上的重要 年頭,本年他非但正式收徒講學,更重要的是他結識了白沙先生的弟子湛若 水,在他們之間相互問學的交往中,陽明顯然已受到白沙心學的較深影響。 他在本年所作的《贈伯陽》一詩中說:“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 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我始悔。”(同上)這說明他既轉道教 之長生為儒家之求仁,同時又收歸大道于人心之內,完成了其心學的第一步 構造。這種構造是在湛若水的幫助下完成的,因而帶有白沙心學的明顯痕跡, 尚未樹立起自己的獨立品格,這從他于次年所寫的答甘泉的詩中可以清晰地 顯現出來:“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fā)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空。無欲見 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同上)他公開承認甘泉在 窮“玄化機”中的巨大作用,還辨析了靜虛與虛寂之空的區(qū)別以及無欲與勿 忘勿助的重要性,這些全是白沙心學的重要命題。可以說,陽明心學在弘治 十八年時已經完成了所有的理論準備,從而達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然而, 盡管他遍讀了考亭之書,熟悉了佛道之理,接觸了白沙之學,并試圖將所有 的義理收歸于心,但他還是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心學體系,原因很簡單,他不 能達到“心與理為一”的程度,也就是說他的學說既不能解決現實的人生難 題,也缺乏自我生命的真實體驗,因而從陽明成圣的初衷看,他的心學理論 尚未完成。在心(自我生命體悟)與理(各種人生哲理)之間,仿佛仍隔著 層薄紙,需要有一個合適的契機將其捅破,從而達到渾融一片的境界。 這一契機終于在正德元年來臨,盡管對陽明本人來說那是個不幸的遭 遇。當時武宗忙于游樂,而造成了劉瑾專權的局面。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 徽等人因諫爭而被逮系詔獄。王陽明乃抗疏相救,結果亦下詔獄,“已而廷 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年譜》一)對于此次進言得 禍,陽明并不后悔,作為一個儒者與在朝臣子,扶傾救危是其份內的職責, 因而當他身處牢房,仰望著從屋頂縫隙中灑下的月光時,所想到的仍是:“良 人事游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 霰。”(《王陽明全集》卷十九,《屋罅月》)當然,在這種逆境中,他也不 得不考慮如何安排以后的人生。根據陽明此時所理解的白沙心學,他顯然有退 隱自全的打算。他在獄中有《讀易》詩說:“《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 保。俯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余樂,此意良非矯。幽哉陽明麓,可 以忘吾老。”(同上)《易·遯九四》爻辭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周易集解纂疏》卷五)其意為心安而退而君子獲吉祥,小人則難以做到。 《易·蠱上九小象傳》辭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同上卷三)亦即退 隱以高尚其志之意。在《王陽明全集》卷十九中收有五十五首所謂的“赴謫” 詩,其中表達歸隱之志的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可知退隱之念并非其一時的心血 來潮。根據當時的危險情景(如在其赴謫途中尚被劉瑾派人追殺),他沒有理 由不產生退避自保的心理。然而,家庭的責任又迫使他不能只顧一己之身, 《年譜》記載當他躲過追殺后,曾有“遠遁”的計劃,但此時他卻遇到了當 年在鐵柱宮相識的那位道士,他勸陽明說:“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 誣以北走胡,南走越,何以應之?”于是陽明遂決定徑往龍場驛所。此一情 節(jié)的可信性也許尚容商量,但是依據陽明當年欲出世而放不下親人,以及其 父因受牽連而罷官的事實,則他當時曾有家庭顧慮應是其真實的情狀。既要 應付險惡的貶謫環(huán)境,又不使家庭受到牽連,還要排除心境的焦慮與不放棄 儒者的氣節(jié)責任,所有這一大堆的人生難題都擺在陽明先生的面前,他需要 動用其全部的知識儲備并進行認真地思考體悟以期得到解決。 正德三年春陽明到達其貶謫之地龍場驛。當時的龍場是一個非常偏僻荒 涼的地方,《年譜》曾描述該地情狀說:“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中,蛇虺魍 魎,蟲毒瘴癘,與居夷人鴂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 之范土架屋以居。”除自然環(huán)境險惡之外,“時瑾憾未已”,因而陽明此刻 “自計得失榮辱皆得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 命而已。’日夜端居澄然,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圣人處此更有 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在這生命的絕境里,他 失去了前此的所有人生憑借,什么先儒的教訓、朝廷的公正,都無助于解決 他眼前的生存困境。無奈之中,他采取了“俟命”的被動態(tài)度,住于石墎之 中,意味著他已抱定等死的決心。為了排除生死的焦慮,他采取了以前曾接 觸過的道家與白沙心學的靜坐之法。在這“端居”的過程中,以前所儲備的 各種人生理論包括格物之論顯然紛紛涌進他的意識之中,最后他終于悟到了 “吾性自足”的人生境界,并由此度過了生命的危境。因而陽明龍場悟道的 除衷并非要建立什么理論體系,而是首先解決其自身的生存危機,這在其作 于正德三年的《五經臆說序》中講的很清楚:“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 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錄之,意有所得皆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 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于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 娛情養(yǎng)性焉耳。”(《王陽明全集》卷二二)陽明所著之書當然有啟示后學的 作用,但論其最初動機,則是為了自我的精神解脫。那么龍場悟道解決了陽 明什么樣的人生難題呢?首先是擺脫了對環(huán)境的依賴,超越了生死禍福的糾 纏與威脅,形成了以自我為價值標準的人生態(tài)度。在這方面,他采取了道家 的生死觀,作于正德三年的《祭劉仁征主事》中說:“死也者,人之所不免 也;名也者,二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tài)萬狀,而必歸于一盡。君子 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同 上卷二八)此類語言一般士人也都頗熟于耳,但陽明此時的言說卻有了全新 的意義,因為通過龍場悟道他已大大提升了自我境界,而這種對生死的認識 也已融入其自我的真實生命體驗,用他本人的話說已經心與理合一。并且他 還將此種人生的境界落實到他的生活實踐中。正德三年,思州太守派人至驛 所侮辱陽明,當地夷民為其不平,毆打了來者。州守大怒,“言諸當道”,友 人毛憲副與陽明陳述禍福利害,并要他去向州守謝罪。陽明絲毫不為所動, 義正詞嚴地寫信說:“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茍忠信禮義之不存,雖 祿之萬鐘,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 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于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 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 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茍欲加害, 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 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同上卷二一, 《與毛憲副》)毛憲副的勸告自然是善意的,但他卻是按當時的官場慣例作 為根據。而此時的陽明已經跳出了此慣例,他不再以官職大小論尊卑,不再 以禍福利害言取舍,不再以外在權威看對錯,他現在已經將價值判斷的權力 收歸于自我。如果堅信自我是正義的,便不會被外來的壓力所撼動;如果他 人以權勢來對自我的正義行為橫加迫害,那么自己也就將其視為瘴癘蠱毒與 魑魅魍魎。此即為心與理為一,此即為以心格物。這即是一種處世的態(tài)度, 又是一種士人的人格理想,在《君子亭記》中,陽明曾借用竹子來說明此種 理想人格的特征:“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 外節(jié)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 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xié)肆夏,揖遜 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屈不撓,若虞廷群后, 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同上卷二三)此無疑是陽明之自 況,既能虛靜以定其神,以闊其心,又能四時而無改其節(jié)操;順時而動,可 出可隱,無不從容自如;既有揖遜俯仰之恭謹,又有挺然特立、不屈不撓之 偉岸,儼然一位圣者之形象。因此,陽明所言的心即理實際上便是我即理, 亦即將價值評判的權力收歸自我。盡管其自我的內容仍然是以忠信禮義為核 心而構成的,但卻極大地突出了主體的地位,從而使士人的人格得以從外在 的權威中擺脫出來而獨立。 不過對陽明本人來說更重要的是,通過龍場悟道改變了自我的心態(tài),即 從憂讒畏譏的悲憤凄涼轉向從容自得。龍場悟道的確是陽明生命的一次巨大 轉折,經由此次轉折,可以說無論是其學術還是生活都具有了全新的意義。 陽明在其《玩易窩記》中形象地描繪了這種轉折的過程:“陽明子之居夷也, 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 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措,孓然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聯(lián)兮其若 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如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yōu)然 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 其夷之為厄也。”(《王陽明全集》卷二三)將龍場悟道喻之為讀《易》我以 為是非常恰當的。這不僅是因為陽明的確曾在此讀《易》以悟解人生,更重 要的是通過此次深刻的反思,他同時也把一部復雜的現實人生的大書悟解透 了。而一旦得悟之后,其精神狀態(tài)也就從原來“茫乎其無所措”的迷亂轉化 為“視險若夷”的從容。嘉靖三十年在龍場為陽明先生建祠時,其得意弟子 羅洪先特撰碑記以志,其中具體地講述了龍場悟道對陽明人格心態(tài)的巨大轉 變作用: 先生以豪杰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于是一變而為文章,再變而 為氣節(jié)。 當其倡言于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 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后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棄流離于萬里絕域, 荒煙深菁、貍鼯豺虎之區(qū),形影孓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 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輾 轉煩瞀,以須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一身之外。至 于是而后如大夢初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 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我獨 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陽明全書》卷三五) 依羅洪先的理解,陽明在龍場悟道之前乃是氣節(jié)之士,而在此之后則真 正具備了圣者氣象。作為士人,氣節(jié)固然重要,李東陽正是因為缺乏氣節(jié)方 才被李夢陽們所不滿,而空同先生正是由于狂直之氣節(jié)受到后世的崇敬。陽 明在反對閹宦專權時,所表現出來的“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的氣節(jié)與空同 如出一轍,故而羅氏亦贊其“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后世”。然而,氣節(jié)之士 又是有缺陷的,即價值取舍往往依賴于朝廷或某些大老、圣賢等外在標準。 一旦失去這些,便沒有了精神的依托,從而發(fā)狂憤激甚至消沉頹廢。李夢陽、 康海們的遭遇幾乎與陽明相同,可他們并沒有從困境中超拔出來,而是走向 了沉淪。羅洪先認為陽明的偉大就在于當他面對生命的絕境時,不僅未走向 消沉,反而更進一格,去掉了原來的僵硬之“強”,不實之“浮”,悟解了外 在權威對自我生命之無益,發(fā)現了自我良知對于生命存在之重要。羅洪先不 愧是陽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對其師的理解顯然是準確的。這只要讀一讀 陽明本時期所寫的詩作,便會由衷地佩服羅氏的上述概括。陽明此一時期的 詩作被稱為“居夷詩”,其中《去婦嘆》五首(《王陽明全集》卷十九)被列 在最前邊,顯然是剛至龍場時的作品,其詩前有小序曰:“楚人有間于新娶 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綣不忘,重無他適。予聞其事 而悲之,為作《去婦嘆》。”詩乃借棄婦以自喻是不言自明的。這種詩,我們 在黃淮那里見過,在李夢陽那里也見過,可以說,明前期的幾乎所有士人都 將自己與君主之間視為是妻妾與丈夫的關系,王陽明的詩文中此種比喻是并 不多見的。此刻他竟然一連寫了五首,則說明當時的他與一般士人并沒有太 大區(qū)別,他尚沒有形成自立的學術品格,他的存在還必須靠朝廷與先圣的支 撐,一旦離開這些,他便會產生強烈的孤獨感,故其第一首曰:“委身奉箕 帚,中道成捐棄。蒼蠅間白璧,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為妍。命 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艷,頹魄不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 還。”他恨間黑白的小人,嘆自身的命薄,因而他有了與先賢屈原相似的委 屈感,在《吊屈原賦》中,他感嘆“世愈隘兮孰知我憂”。(同上)在作于正 德元年的《咎言》中,他更喊出“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余之衷?”(同上) 但他不能怨君心,不敢忘“君子賢”。在尋不到出路時,他也曾象其他貶謫 士人那樣用痛飲來麻醉神經:“污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同上)以忘卻 心頭的煩惱。但是當他身處荒涼險惡的境遇中時,其人生的體驗顯然要比原 來復雜得多,加之其前期的思想積累,逐漸對此種妻妾地位萌生了懷疑,因 而在第五首中說:“空谷多凄風,樹木何瀟森!浣衣澗冰合,采芩山雪深。 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巑岏隔 云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同上)“別鶴操”一名“別鶴怨”,相 傳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命其休妻再娶。牧子悲傷作歌曰:“將乖比 翼隔天端,山川悠悠路漫漫,攬衣不寐食忘餐。”后人為之譜曲,名《別鶴 操》,以喻夫妻分離。(見崔豹《古今注·音樂》)“孤鴻”應為“孤鸞”, 陶淵明《擬古九首》其五曰:“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陶淵明集》 卷四)可知二曲皆為傷別離之意。在本詩中,陽明雖依然自比棄婦,依然哀嘆 憂思,但在凄苦境遇的折磨下,終于開始對“君聰甚明哲”的信念產生動搖, 因為在這所謂“甚明哲”的時代,又何以能夠有“聞此音”的不幸呢?這種 對“明哲”的懷疑,應該是陽明先生之人格走向獨立的信號,也是他心學產 生的契機。果然,經過自我痛苦的思索,當他讀懂了時代人生這本復雜如 《易》的大書之后,當他體悟到只有自我的良知才是最終的生命依托之后, 他豁然開朗了,于是再看他悟后的《諸生夜坐》一詩,便是迥然不同的另一 種情調了: 謫居澹虛寂,眇然懷同游。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疇。草際見數騎,取 徑如相求; 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騶;投轡雁騖進,攜盒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 蠟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村翁或招 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為謀。 (同上)平靜的語氣,疏緩的節(jié)奏,內容豐富的生活,從容自得的情調,顯 示出陽明擺脫棄婦心態(tài)后的樂觀心境。這種喜悅不僅是因為有了朋友來往而 不再孤獨,有了師生的講學活動而沖淡了郁悶的心情,更重要的是人生情趣 的改變與人生境界的提升。他的講學活動不再是正襟危坐的枯燥訓示,而是 伴隨著鳴琴的和樂與投壺交杯的自由瀟灑。除講學外,夜弄溪月、曉陟林丘 的自然之樂,村翁招飲、偕客探幽的優(yōu)雅之趣,都使他充分感受到人生的可 愛可樂,以致令他想起了當年被孔子喟然而嘆的曾點之樂。這種情趣不是陽 明偶而有之的一時之舉,而是常常出現在其詩作中,如:“富貴猶塵沙,浮 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同上《諸生》)“交游若問居夷 事,為說山泉頗自堪。”(同上《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漸覺形骸 逃物外,未妨游樂在天涯。”(同上《南庵次韻二首》其一)可見環(huán)境并未有 變,而是心境有了改變,依然是貶謫生活,依然是遠山僻水,依然是遙遠天涯, 但由于視富貴如塵沙,等浮名于飛絮,故而便覺得山泉可喜、天涯可樂了。這 正如他在勸朋友時所說的:“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 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只要能得“虛舟”之意,亦即具備一副超越的襟 懷,則便會“隨處風波只宴然”了。(同上《贈劉侍御二首》)從憂讒畏譏到 心情無處不宴然,陽明的確使自我生命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關于陽明龍場悟道的意義,以前往往從其心學建立的方面談了很多,這 當然是大有必要的。但就王學的理論內涵看,王陽明在此一時期并未留下太 多的有價值著作,比較成形的是前面曾提到的陽明用以“娛情養(yǎng)性”的《五 經臆說》,但陽明本人并不同意將其流傳,當弟子錢德洪為其師“不復出以 示人”而遺憾,并要求其傳世時,陽明卻說“付秦火久矣”。直至陽明逝世 后,錢氏才從其師的廢稿中搜得十三條而公布于世。從這十三條殘存稿來看, 不能說毫無價值,如其釋《左傳》“元年春王正月”曰:“故元年者,人君為 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 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同上卷二六,《五 經臆說十三條》)這顯然是針對武宗即位后的荒唐行為有感而發(fā),表現出正 君心的心學格物特征。但正如陽明本人所說;“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 端曲學,如執(zhí)權衡,天下輕重莫逃,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同 上)就是說《五經臆說》并非心學的成熟著作,因為它不符合心學求悟的根 本精神。因而龍場悟道從心學的學術意義上講,可以視為是其起點,或者說 是陽明思想轉向的標志。但龍場悟道還有比學術本身更加重要的意義,對此 已有人作出過頗有價值的論述,⑥現再進一步作出強調。對王陽明本人而言, 龍場悟道的意義在于:他一方面動用前此所掌握的禪、道二家的修煉功夫, 解決了他遇到的實際人生難題,即當其身處逆境時,得以超越外來的諸種威 脅而保持心境的平靜空明,從而使其避免陷入悲觀沉淪;同時他又以儒家的 心學理論(尤其是從湛若水那里了解的白沙心學),提升了禪、道二家的人 生境界,即擺脫精神苦悶的目的并非完全為了一已的自我解脫,而是為了保 證其在艱難的境遇中擔負起一個儒者應有的人生責任,這包括關懷他人,留 意國事,講學不輟,保持自我節(jié)操等等。可以說,陽明先生通過龍場悟道, 用釋、道的超越理論應付了險惡的環(huán)境,又用儒家的責任感堅定了自我的用 世之心。從明代士人的人格心態(tài)演變史的角度看,王陽明的這種人生體悟與 心態(tài)轉變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它顯示了明代士人正在開始艱難地擺脫長期 的從屬地位,從原來政治工具的角色轉向道義的承擔者,從妾婦的心態(tài)轉向 獨立自主的心態(tài)。當然,這個轉變過程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且終明之世 士人也很難真正完全獨立。但王陽明畢竟向士人昭示了一種新的人格形態(tài), 為士人擺脫現實苦惱提供了一種內在超越的有效途徑。盡管它未能及時地成 為醫(yī)治李夢陽、康海們精神苦悶消沉的良藥,但在以后的歷史發(fā)展中則顯示 了極大的活力。正如具有同樣遭遇的顧璘所言:“謫來頗與靜便,唯思親一 念,唯日耿耿。正思執(zhí)事談滇中之樂,于時漫為悲喜。廼今始知其味也。” (顧璘《息園存稿》卷八《與王伯安鴻臚》)盡管顧氏并不算王門弟子,卻 也用陽明龍場的人生體驗來解決貶官的精神苦悶。陽明后學鄒元標在萬歷時 期同樣體驗了講學對其人生自我生存的意義:“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 游,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之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 菁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馀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 (《明文海》卷六一,《講學疏》)其實,以心學度過精神危機者比比皆是, 舉顧、鄒二人只不過例示說明而已。當然,陽明心學并非只為士人提供緩解 心靈危機的藥方,而是還有更為重要的目的,但就龍場悟道而言,我以為主 要意義便在于此。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