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nbgc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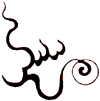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嘉靖朝在明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前人對此曾有過許多明 確的表述,在風俗方面,“正、嘉以上,淳樸未離。”(《四庫全書總目》 雜家類存目九《續說郛》)而此后則變為奢侈放縱。在士人人格方面, “當正、嘉之際,士大夫刓方為圓,貶其素履,羔羊素絲之節寢以微矣。” (《明史》卷二0一,贊語)亦即由原來的方正守節而變為圓滑不講原則。 從學風方面,“弘、正以前之學者,惟以篤實為宗。……至正、嘉之間, 乃始師心求異。”(《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一《雅述》)在學術方 面,“朱、陸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 朱學之拘。正德以后,則朱、陸爭詬。隆慶以后則陸竟勝朱。又久厭陸學 之放,則仍伸朱而絀陸。講學之士,亦各隨風氣以投時好。”(同上子部, 儒家類存目,《朱子圣學考》)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了嘉靖朝作為轉折標 志的特征。那么,在這一時期,朱、陸(實即王學)之間相互消長的具體 情況如何,它們與士風的變化有何關系,王學在士人心態的流變過程中起 到了什么作用,這便是本章所要解決的問題。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是對 嘉靖朝的政局變遷、士人人格的變異、以及陽明心學在此時的遭遇與其所 扮演的角色的研究,以期為全章的論述構畫出一個清晰的時代景觀;第二 節是對王艮及其所開創的泰州學派的研究,主要著眼于他們所提出的出位 之思、守道尊身的理論以及由此形成的狂俠精神,意在強調陽明心學在新 的時代境遇中如何熔鑄了新的士人人格,從而對時代作出有效的回應;第 三節是對羅洪先及其聶豹歸寂理論的探討,意在強調士人在險惡的政治環 境中所采取退隱自保的另一人生價值取向的追求,同時指出了其有別于傳 統隱士的心學特色;第四節是對王畿心學理論與人格心態的研究,主要是 指出其“圓而通之”的理論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出世與入世兼顧的 價值取向,以及如何在現實中向著求樂自適的人生態度而傾斜,意在強調 其所顯示的明代士人人格的新特征;第五節是對唐順之心學思想、文學思 想與人格心態的研究,主要是突出其從狂者人格向中行境界的努力與轉變, 同時辨析了其晚年出山御倭的性質與意義。 第一節嘉靖朝政治與士風演變以及王學之遭遇 一、“大禮議”對嘉靖士風之影響與王學所扮演之角色 “大禮議”是嘉靖朝所遭遇的第一件大事,也是對該時期士風影響巨 大的歷史事件,因而在明史研究中歷來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然而從士風演 變的角度,尤其是王學諸人在其中所采取的態度及其作用,盡管近幾年來 也有人略有涉及,但尚未觸及問題之實質,而此事件實關涉到對嘉靖一朝 士人心態之研究與王學性質之判定,故須詳加申說。 所謂“大禮議”是指朝廷如何對待世宗之生父興獻王之稱呼與地位的 爭論。武宗因一生荒唐放蕩,故在二十九歲時即早早病逝,并且未留下任 何子嗣。按明代兄終弟繼的祖訓,興獻王乃憲宗之第二子,孝宗之親弟, 其子朱厚熜乃武宗之堂弟,因而群臣在討論武宗之繼承人時,朱厚熜便成 為首選對象。盡管武宗病逝時朱厚熜已繼興獻王之位,但由于他是老興獻 王的獨生兒子,也就責無旁貸地成為了武宗的繼承人。但他即位后面臨的 頭等難題便是如何安排其生父的地位。以顧命大臣楊廷和為代表的文官集 團堅持繼統兼繼嗣的意見,認為世宗應該以孝宗為“皇考”,而以興獻王 為“皇伯考”。但世宗卻又是興獻王的獨生子,如果過繼給孝宗為子,豈 非又絕了興獻王之嗣?于是,雙方互不相讓,且文臣后來也分為兩派,從 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最后則是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集團的失敗 而告終。就人之常情而言,讓世宗絕己父之嗣而為他人之子,在心理上總 是難以接受的,故而當禮部告知其廷議結果為“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 為皇叔父母”時,世宗立即表示不能接受說:“父母可移易乎?”(《明史 紀事本末》卷五十)在學識淵博的文臣們引經據典的決議面前,世宗當然 講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既成的結論。而且開始時 他既沒有準備也沒有能力與群臣作強硬的對抗,他想通過求情使文臣們讓 步,因而說:“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 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同上)又據《明史》卷一九 一《毛澄傳》載:“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 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 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 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不允。”在這以君主身份而以金 賄臣與近乎哀求的語氣中,很難說不含有世宗父子間的真實倫理情感。難 怪當他看到張璁支持其推尊父母的《大禮疏》時,會異常激動地說:“此 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同上卷一九六,《張璁傳》)無奈楊廷和諸人態 度異常強硬,一開始便擺出無絲毫通融馀地的架勢,盡管世宗“每召廷和從 容賜茶慰諭”,然“廷和卒不肯順帝指”,并“先后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 三十疏”。(同上卷一九0,《楊廷和傳》)甚至公然說“異議者即奸邪當 誅。”(《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禮部侍郎王瓚表示異議,便立即被逐至 南京禮部任侍郎;繼之支持世宗的張璁也被安排在南京禮部供職。雙方的互 不相讓導致了沖突規模的越來越大,始而是抗旨封還御批,既而是上疏辭職, 最終是大規模的群臣抗議。而隨著部分文官站出來支持皇上,世宗的態度 也愈益強硬,始則允其辭官,既而懲罰個別文官,最終是將嘉靖三年七月 參加抗議活動的134人抓進監獄,另有80余人姑令在家待罪。然后給以或戍 邊或廷杖或罰俸的處置,其中有17人被杖死,而且凡是因大禮議遭流放者, 后來均很難再有重新起用的機會。 如果就事論事,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們為議禮而造成如此重大的損失 似乎有些不值,而且其行為本身也頗顯迂執,因而也就招致了后人不同的 評價。明人徐學謨曰:“史道下獄,廷和乞罷。累旨慰諭,可謂優渥。乃 請辭五六而不休,至毛紀、蔣冕、林俊、孫文、彭澤、喬宇相繼求去。一 時大臣,未免高激成風,失事幼君之體。自后邪人伺隙離間,新進用而老 成削跡矣。”(談遷《國榷》卷五四,世宗嘉靖八年)明人李贄的評價則稍 微客氣些:“予謂公知識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惟恐陷主于非義,則 精忠貫日可掬也。”“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 (《續藏書》卷十二,楊廷和)清人谷應泰則各打五十大板說:“若夫廷和 等之伏闕呼號,甚于牽裾折檻;世宗之疾威杖戍,竟同元祐黨人。大禮未 成,大獄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譏焉。”(《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仿佛 雙方均不夠冷靜,將一件本來可以好好商量的事激化為不可收拾的君臣沖 突。從表面看,楊廷和諸人的確有些膠柱鼓瑟而不近人情,當他們說:“大 禮關系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同上)時,似乎真有些小 題大做,故而有學者指出楊廷和諸人為“迂闊固執不化的儒生”。①然而, 從歷史事實的角度上看,對楊廷和的如此判斷卻并不完全正確。楊廷和 (1459—1529年),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時年只有十 九歲。史書言其“為人美風姿,性沉靜詳審,為文簡暢有法。好考究章故、 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負公輔望。”(《明史》卷一九0,《楊廷 和傳》)這顯然與迂腐固執不相干。他在正德年間繼李東陽為首輔,在那 風云變幻的多事之秋,面對荒唐而不負責任的明武宗,周旋于倖臣閹宦之 間,盡管未能取得更為顯赫的政績,卻也實屬不易。尤其是在武宗病逝之 后的一段時間內,朝廷權利一度出現真空狀態,楊廷和曾主持朝政近四十 余日,他用計擒獲了江彬等奸佞之臣,保持了政局的平穩;又迅速確定了 皇位繼承人,使得政權實現了順利交接;還通過遺詔的形式,革去了武宗 時期留下的各種弊政。拿楊廷和如此的精明干練,很難設想他不知道與皇 上對抗將會具有何種后果。即使楊廷和一時糊涂,也很難解釋數百名京官 的態度何以能如此一致,都甘愿以身家性命做賭注,跟隨他一起去與皇帝 抗爭。其實,稍微了解明代歷史尤其是正德朝歷史者,都會明白楊廷和等 人此種舉措的不可避免,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意義。在整個正德一朝, 由于武宗的喜好游蕩娛樂,導致了多么可怕的政治結果,而在文臣的心目 中,武宗之所以如此放蕩不羈,肯定與其未能得到足夠而有效的儒家教育 分不開。現在新皇上剛剛登基,若不加以及時的教育與有效的管束,誰又 能保證他不會成為第二個明武宗呢?更何況楊廷和身為顧命大臣,手中握 有實權,只要文官集團能夠保持一致,理應可以將新皇上納入儒家所設計 的圣君模式。從實質上講,大禮議可以視之為是帝王之勢與儒者之道的一 次較量。當楊廷和之子楊慎向群臣高喊:“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 正在今日。”(《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其心中所擁有的崇高悲壯感覺, 儼然與當年方孝孺面對成祖朱棣時一樣義正而辭嚴。對于論爭的這種性 質,世宗本人也不會毫無所知。盡管他當時只有十五歲,可他身邊的藩邸 謀臣袁宗皋輩則肯定會及時地提醒他。因為皇上與群臣之間的權力較量不 僅體現在議禮之中,也體現在朝政的諸多方面。如嘉靖元年九月,在文官 集團與世宗之間曾發生了是否罪內臣的爭執,談遷《國榷》記曰:“前命 科道部曹核御馬草場地,逾年盡得其私。奏上,戶部請罪內臣。上意宥之。 是日,日講罷,諭輔臣:‘草場事勿竟。’楊廷和曰:‘此最為先朝之累, 侵官民田幾萬頃,毀人冢亡算。不罪之何以示后?’明日,降罰舊內臣有 差。”(卷五二)此事之詳情已不得而知,若就事論事,文官們自然是對的, 而且最后也終于按他們的意思了結了該事。然而,世宗開始時何以要“宥 之”,他實際上并沒有充足的理由去保護這幾位內官“舊臣”,根據后來輕 易地便將其“降罰”來看,世宗也的確沒有表現出什么特殊的興趣。這便 有理由相信,世宗“宥之”的舉措只是一種姿態,或者說是一種試探,他 要看一看文官們對其圣意究竟會采取何種態度。楊廷和當時手中握有重 權,自然很輕松地壓制住了世宗。然而,這顯然會在世宗的心靈深處留下 一絲雖則輕微卻又難以忘懷的不快,加之他那由外藩入京繼位而造成的敏 感心理,這便使得世宗鞏固加強皇權的念頭日趨強烈,則后來的大禮議也 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尤其是當他發現文官集團的態度如此強硬,他的商 議求情竟然絲毫無濟于事時,也就不能不采取同樣的強硬態度,無論是他 涕泗不止地要“避位奉母歸”,還是聲色俱厲地大叫“爾輩無君,欲使朕 亦無父乎?”(《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均顯示了他心中所長期積蓄的 怨恨情愫。直至嘉靖七年世宗在為大禮議定案時,他所不能忘懷楊廷和的 仍是:“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同上)盡管他對楊廷合的感 情是比較復雜的,因為沒有楊廷和的推舉,他便不可能以外藩的身份登大 寶君臨天下,所以最終他對楊氏只給了“特寬宥削籍為民”的處罰;但是 他決不能被輕視,甚至不能被任何人所限制,這是自太祖以來便形成的傳 統,已深深印刻在每一位朱氏皇族成員的心頭,因而從此一角度他對楊廷 和又充滿了仇恨,所以才會咬牙切齒地說楊廷和“法當戮市”。(同上)在 明代歷史上,大禮議是士人以“道”抗勢的舉措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同時 也是失敗最為慘重的一次。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當即喪命杖下,還有更多 的人被罷職貶官流放,從此永遠結束了他們的政治生涯。那位曾高叫過“仗 節死義,正在今日”的楊升庵先生,不得不將自己的所有政治熱情與橫溢 才華消磨在荒遠滇南的吟詩作賦之中,他有一首《自贊》詩說:“臨利不 敢先入,見義不敢后身。諒無補于事業,要不負乎君親。遭逢太平以處安 邊,歌詠擊壤以終余年。天之顧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 沖而盈,寵為辱,平而福者耶!”(《升庵集》卷十一)詩中所言可謂半真 半假,半真是指他堅信自己的人格高潔無瑕,盡管其政治生涯以失敗而告 終,但他自認為無負于君親,無負于道義;半假是指他不得不表示平靜地 接受這種流放的處罰,以免再招致更多的麻煩。據錢謙益所記:“用修在 滇南,世廟意不能忘,每問楊慎如何。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用修聞之, 益自放。”(《列朝詩集小傳》丙集)于是他在滇南便留下了諸多瘋癲放浪 的佳話,焦竑《玉堂叢語》載:“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 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為怍。”此可謂是其“自放” 的最形象地說明,但焦氏卻不同意其目的是佯狂避禍,故曰:“人謂此君 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 耳。”(卷七《任達》)其實,錢、焦二人所言均有道理,楊慎在得禍之后, 他深知世宗對其父子的忌恨情緒,而不得不采取應有的措施;而在漫長的 流放生涯中,他又必須用各種方式去排解心中的苦悶與不滿。因為他沒有 接受王學我心自足的理論,也就不得不走上與李夢陽、康海們一樣的狂放 之路。所不同的是,這次他們得罪的不是如劉瑾般的閹宦,而是皇上本人, 也就更少有平反的機會,尤其是這位明世宗竟然在位長達四十五年,這意 味著這群文人在其有生之年再難有出頭之日。不過,這依然不是大禮義影 響的全部。在世宗這方面,他不僅從此次事件中對文臣們產生了忌恨的情 緒,以致使他在以后的生涯中很難與臣子們處于一種和諧融洽的政治關系 中。更重要的是,通過此次事件,使他深深懂得了權力的重要,由此便造 成了世宗人格上的兩大特征:一是強烈的專制欲望。在他后來的政治生涯 中,他從來不肯對權力有絲毫的放松,哪怕是后來在他迷戀上求長生的齋 醮后,也從不放松對權力的把持。對權力的過分迷戀又導致了他敏感多疑 的心理,從而不相信任何人,在情感上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二 是對個性突出的臣子的忌恨與反感。在嘉靖一朝中,凡是被世宗認為具有 狂放自恣傾向與個性的官員士人,無一不遭致重罰。所有上述這些影響, 都決定了嘉靖一朝的政治格局與士人的地位,因而大禮議無疑是本朝最重 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然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文官集團抱著如此堅定的決心去與皇上 抗爭,何以會遭致如此徹底的失敗?從明代皇權所達到的空前膨脹的情形 而言,似乎一開始便注定了文官集團失敗的命運。但也不盡然,因為雖然 同樣是遭到失敗,卻具有各種各樣的失敗方式。萬歷時期的張居正盡管死 后被抄家清算,也是以失敗而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但他生前畢竟大權在 握了整整十年。而楊廷和實際上只與世宗對抗了不到三年的時間便已徹底 敗下陣來。也許不應該將世宗即位時比神宗大了六歲此一因素看得過重, 因為他畢竟還有以外藩繼統的不利因素存在。我以為此次文官集團失敗的 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其內部出現了分裂,而分裂的原因則是學術思想的相 異。具體地講,也就是程朱之學與陽明心學的不同。可以設想,假如沒有 張璁、桂萼、方獻夫、席書、黃綰、黃宗賢諸人的支持,以及在理論上為 世宗尋到堅實的根據,世宗怎么能夠顯得如此信心十足而不向群臣屈服? 正如李贄所言,不應該懷疑楊廷和等人忠于朝廷的愿望與堅守道義的決 心。楊慎等人明確地表述了他們的觀點,《明史紀事本末》曰:“修撰楊慎, 廷和之子也。率同官姚淶,編修許成名、崔桐,檢討邊憲、金皋等上言: ‘君子小人不并立立,正論邪說不并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 萼等所言者,冷褒、段猶之余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恥與萼等并 列。’”(卷五十)堅持考孝宗的楊廷和諸人的確是引證了宋儒程頤在宋濮 安懿王繼仁宗位而考之一事上的議論,毛澄曾引程頤之言說:“為人后者, 謂所后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明史》卷 一九一,《毛澄傳》)故而楊廷和本人也說:“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 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議禮之正,可為萬世法。”(《明通 鑒》卷五一,嘉靖三年六月)他們盡管未能從朱熹那里找到直接根據,但 在精神實質上應該說是完全一致的,即明正統、正綱常而棄私恩。而幾乎 所有支持世宗考其生父的人均是從父子之情而出發,張璁說:“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乎? 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同上卷四九,正德十六年七月) 方獻夫說:“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 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 臣度以為不然。”(同上卷五十,嘉靖元年五月)這種觀點顯然是與陽明心 學的精神相一致的,這從相反的例子中亦可得到說明,王門弟子中也有追 隨楊廷和觀點的,最突出者為鄒守益。鄒守益(1491—1562),字謙之, 號東廓,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大禮議時因上疏憮 旨而被下詔獄,后被謫判廣德州。在嘉靖五年陽明給鄒氏的信中,曾詳細 地談了對禮的理解,他說:“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 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 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議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 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 察者矣。后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 萬古如一日。茍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 蕢矣”。(《王陽明全集》卷六《寄鄒謙之》二)目前尚無充足的材料證明, 陽明此段話是在有意開導這位當初曾反對世宗考其親父的弟子應修正自 己的觀點,但他的看法顯然是與張璁、方獻夫諸人完全一致的。結合陽明 弟子陸澄的事例或許更能說明問題,《明史》載:“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 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逮服闕入都,《明倫大典》已定,璁、萼大用事, 澄乃言初為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 而帝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卷一九七,《黃綰傳》)《明 史》的本段論述,顯然是來源于徐學謨對陸澄的攻訐,這在《明儒學案》中 黃宗羲已辨之甚詳,不必贅言。②然由此二例足以說明,陽明心學之思想實 與張璁諸人相一致。在議禮雙方的爭辯中,盡管也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比 如廷和一方有借先儒之權威而迫使世宗就范的意味,而張璁一方也有象桂 萼等人那樣,具有借議禮以求顯達的政治投機目的,但在學術思想上的確 可以視為是朱子學與陽明學的首次正面交鋒,而最后以正統的程朱理學的 失敗而告終。這其中不僅僅是因為張璁一方有世宗的支持才具有了優勢, 而是楊廷和一方所堅持的程朱理學已顯得過于僵化,而陽明心學則更合乎 人之常情。比如當張璁的《大禮疏》上奏朝廷后,盡管并沒有馬上得到多 數人的支持,但有不少人私下已感到其見解的合理,當時尚在家居的大臣 楊一清看到《大禮疏》后,曾立時致書吏部尚書喬宇說:“張生此論,圣 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南京吏部尚書石珤也暗自告訴張璁說:“慎之! 《大禮說》終當行也。”其實,就是楊廷和本人也感到了張璁《大禮疏》的 咄咄逼人,盡管他授意吏部將張氏逐出京城,使其到遙遠的南京去充任閑職, 可依然覺得不放心,便寄語張璁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為《大 禮說》難我耳”。(《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威脅的語氣中又分明包含著 乞求的意思。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就是如此,明知自己所堅持的思想信念已 不如爭辨對手,卻依然固執而不肯改變初衷,于是便不能不得到一個雖則 悲壯卻必然失敗的結局。關于大禮議思想背景的問題,近來已有人專門撰 文加以討論,盡管其中還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但其所概括出的“天理”與 “人情”的爭論核心,仍舊具有較強的說服力。③故筆者對此不再多加討 論。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大禮議決不僅僅是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間的學 術爭論,而是充滿了許多復雜的因素。對此,通過陽明及其弟子在大禮議 中的復雜心態,可以得到很好地說明。據王陽明年譜記載,大禮議開始后, “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后皆以大禮問,竟不答。”(《王陽 明全集》卷三五,《年譜》三)陽明為何不回答弟子的詢問,這是個值得 深究的問題。其實年譜所言并不準確,大禮議高潮時陽明雖未明確回答弟 子,但在嘉靖六年他還是在給霍韜的信中較詳細地對此作出了解釋:“往 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 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 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于天下,俟信從者眾,然后圖之。其后 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 為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后來賴諸公明目 張膽,已伸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去,而病勢亦甚危 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同上卷二一, 《與霍兀厓宮端》)在此段話中,陽明言其未回答弟子之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對當事者已失去信任,認為他們不會聽從自己的意見,還不如先講明 于天下,造成輿論的壓力,然后再作主張;二是自己正處于被他人攻訐的 不利情形中,言之恐難以產生應有的效果。這些盡管都是陽明的心里話, 但我以為又都不是其根本原因,陽明最擔心的是他在信的結尾所指出的, 因“倒倉滌胃”的折騰而使元氣大傷,也就是說使士人遭致嚴重的摧折。 這種擔心并非是在事后才被陽明所察覺,而是他人尚正處于爭論的興頭上 時,他已經預測到了事件將會產生嚴重的負面效應。他在嘉靖三年曾用兩 首詩暗示了此種心情: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 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 塵。(《碧霞池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 春。千圣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不及惺惺陋巷 貧。(《夜坐》)(《王陽明全集》卷二十) 王陽明年譜說“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同上卷三五)至 于此所言之“微”為何意,卻從未有人解說清楚。其中第二首較好理解, 除了強調“千圣本無心外訣”的自信良知外,最后一聯詩句,則表現了對 于一時紛紛擾擾的爭論已無甚興趣,反不如隱居山中自得其樂為妙。最易 產生誤解的是前一首,有人曾認為“誰與青天掃舊塵”是表現了王陽明在 大禮議初起時躍躍欲試的心情,并以此為題撰寫了論文,似乎陽明及其弟 子一開始稀里糊涂地受了世宗的利用。就實際后果而言,世宗的確利用了 心學。但陽明卻并不糊涂,他在大禮議上當然傾向于滿足世宗的父子之情, 故而才會在給霍韜的信中表示“心善其說”,但他更擔心雙方的爭論將導 致兩敗俱傷的后果,“無端禮樂紛紛議”并非只表示對楊廷和一方的不滿, 而是對爭論本身的擔心與厭倦,因此“誰與青天掃舊塵”也不是要躍躍欲 試地去掃除楊廷和之輩,而是擔心在兩敗俱傷后還有誰去掃除武宗朝留下 的諸種弊端,從而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太平。此處所言青天決非指世宗, 而是陽明心目中的政治理想。盡管楊廷和曾嫉妒陽明之功而阻止朝廷對其 封賞,但陽明依然不希望以他為首的士人群體遭致摧殘,這便是陽明的眼 光與胸襟。這當然不是臆測,因為這不僅有“無端”二字作為其心存厭煩 的內證,而且在他后來與霍韜的信中所擔心的“倒倉滌胃”的后果也再一 次得到了證明。其實,這倒不是說陽明先生具有神奇的預測功能,而是明 眼人均可察覺的事實。南京吏部郎中鄭善夫在嘉靖二年秋曾作《愍竹賦》 曰:“何金玉之瑯瑯兮,乃變此殺伐之余酷。皇天震怒茍罔不摧折兮,松 柏則介而獨留。余悲夫同類之相攻兮,況復值此凜秋。麗洵美于三益兮, 溯前古而則爾。吾清明之內懼兮,蓋君子而相詆。嗟芝蘭之難容兮,荊棘 麗而附薋。縱向昔之非同好兮,不愈于槿蒺之與菉葹。”(《少谷集》卷一 上)少谷先生在此顯然是以竹作喻,指出議禮雙方士人均為有氣節之君子, 而將會出現的兩敗俱傷的慘象實在令人悲傷。此種感覺應該說與陽明是完 全一致的。在歷史上此類旁觀者清的現象也許不值得大驚小怪,但身處其 中者也并非毫無所覺。嘉靖三年八月己亥,“禮部尚書席書奉趣入朝,行 至德州,聞廷臣伏闕哭爭,盡系詔獄,因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為聚訟, 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俾自新。’” (《明通鑒》卷五一)可知王學弟子并無趕盡殺絕之意,其擔心摧折士人 之用心亦甚明。而且待大禮議定后,他們并未象桂萼那般欲致對手于死地, 而是盡量減少士人之損失。如焦竑《玉堂叢語》載:“霍韜自以進賢為己 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仇。推升霍賜,奏錄梁次挹,俱內舉之人也。 薦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皆大禮大獄得罪,陸粲則攻擊公與張、桂 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疏薦王守仁平宸濠、平田州思恩八寨功,及 薦王瓊之政事優長,王九思、康海、李夢陽之文章古雅,其推賢讓能有如 此。”(卷三《薦舉》)霍韜之所以不避恩仇而大力薦舉,不僅僅說明他是 舉動光明的君子,同時更顯示了他廣薦人才以“扶養元氣”的苦心,盡管 他終未能取得“回陽奪化之妙”的實效,其廓然大公之用心則亦可昭日月 矣。 嘉靖七年六月,《明倫大典》修成,這代表著大禮議的結束。盡管其 影響在后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依然存在,但該大典仍可視為此事本身完成的 一個標志。結果是楊廷和一方得到了處罰,張璁諸人得到了褒獎升遷,而 世宗不僅得以稱其親生父母為皇考、圣母,并為他們加了尊號,其父為“恭 睿淵仁寬穆純圣獻皇帝”,其母為“章圣慈仁皇太后”。此種結果似乎勝負 清晰,優劣分明,但實際上卻充滿了復雜的因素。當時被治罪的楊廷和一 方,盡管他們所依據的理論有僵化生硬之弊,但其守道的勇氣與堅定的氣 節則得到了后世的稱揚,尤其是他們以集團的形式對皇權進行了聲勢浩大 的抗爭,為明代士人譜寫了一曲悲壯之歌。而支持世宗的一方盡管在當時 取得了勝利,卻往往被后人指為奉迎帝王,以圖倖進。這當然有一定的道 理,因為其中的確有如桂萼之類的倖進之徒,《明史》言其“性猜狠,好 排異己,以故不為物論所容。”(卷一九六,《桂萼傳》)應該說基本符合 歷史事實。但如果將支持世宗者均視為如桂萼一般,則又是一個很大的錯 誤,如霍韜在嘉靖七年六月大禮成后被超拜為禮部尚書,是當時六部長官中 公認的最重要職位,但他并沒有喜悅的感覺,反而上奏說:“今異議者謂陛 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茍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 意。臣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茍 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為非,何以塞天下口。”(同上,《霍 韜傳》)這的確不是在做官樣文章,因為盡管世宗不允其辭官,可他硬是 三上辭呈并最終得以實現。在此,也充分顯示了霍氏守道的決心與坦蕩的 胸襟。因而對大禮議雙方用小人與君子的標準來判斷是非常不合適的。用 心學與理學的對抗來概括這場爭論,在顯示雙方所擁有的思想系統上也許 比較簡潔明快,但也不能被視為是無懈可擊的概括。因為在楊廷和一方, 也有鄒守益、陸澄等王門弟子廁身其間;而在張璁一方,并不是王門弟子 最先向對方發難,而且作為王學首腦的陽明先生始終不肯介入這場爭論。 因而也就很難用學派間的爭辯來界定此事的性質。更何況在這爭論的過程 中,還有世宗這一更重要的因素存在其中呢?從楊廷和一方的初衷講,他 們的確是要通過對正統與理學的強調,使朝政納入一種更加穩定有序的機 制,然而他們卻徹底地失敗了。他們的失敗不僅意味著士人的皮肉之苦與 氣節之摧,同時也意味著程朱理學的被削弱從而失去了原有的一統局面。 從王門弟子的角度講,他們參加大禮議是因為確實認識到人情比天理更合 乎真實的人性狀態,認為“禮本人情”更符合禮的本義,也更有利于現實 的社會教化。他們依靠這種更令人信服的“人情”擊垮了對方僵硬的“天 理”,卻同時也摧垮了激昂的士氣,而且也未能帶來一個更具有“人情” 味的政治局面,隨之而來的反倒是一個“非天子不議禮”的獨裁結果,甚 至比那個僵硬的程朱理學更為可怕與不合乎“人情”。其實,許多歷史事 件都是如此,表面看似簡單,實際甚為復雜,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觀照會得 出不盡相同的結論,并且很難用單一的是非優劣標準加以判定,但這往往 更接近歷史的真實狀況。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