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nbgc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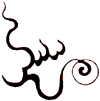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xué)與中晚明士人心態(tài)》 |
|
|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tài)與王學(xué)之流變 第二節(jié) 王艮——儒家狂者的典型 對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xué)派的研究已經(jīng)有許多的成果,其主要觀點(diǎn)大 致有三種:第一種認(rèn)為是所謂的“自我中心主義”,或者叫“個(gè)人主義”, 這是四十年代嵇文甫先生在其《晚明思想史論》一書中提出來的。第二種 是所謂的“世俗化儒家思想”,持此種看法的人很多,恕不一一列舉其代 表。第三種是近些年產(chǎn)生的說法,即重感性的市民化傾向,尤其是將王艮 與其后學(xué)顏山農(nóng)、何心隱聯(lián)系起來論述時(shí),更容易得出此種結(jié)論。這三種 觀點(diǎn)當(dāng)然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前兩種,可以說的確概括出了泰州學(xué)派 某個(gè)方面非突出特征。但如果從王學(xué)與士人心態(tài)的關(guān)系此一角度講,上述 概括顯然是無助于研究的。我以為,無論是從認(rèn)識該學(xué)派的基本性質(zhì)上, 還是對其主要成員的心態(tài)研究上,仍以黃宗羲《明儒學(xué)案》中的意見最為 中肯,他說:“陽明先生之學(xué),有泰州、龍溪而風(fēng)行天下,亦因泰州、龍 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shí)時(shí)不滿其師說,益啟瞿壇之秘而歸之師,蓋 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后,力量無過于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 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nóng)、何心 隱一派,遂復(fù)非名教之所能羈絡(luò)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 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為非其 聰明,正其學(xué)術(shù)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 古人,后不見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dāng)機(jī)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 諸公赤身擔(dān)當(dāng),無有放下時(shí)節(jié),故其害如此。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 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dāng)時(shí)爰書節(jié)略之,豈可為信?”(卷三二)黃 宗羲顯然是不同意顧憲成所言“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的,故而他在 下面為顏鈞、何心隱、鄧豁渠等泰州后學(xué)立傳時(shí),而只強(qiáng)調(diào)了其狂俠行為 與醉心禪門的兩種特征。因而在此也就有必要指出,說泰州學(xué)派有追求利 欲與感性的市民傾向證據(jù)是不充足的,起碼此類特征并非其主導(dǎo)傾向。在 對黃氏此段話的理解中,關(guān)鍵在于認(rèn)清“赤手搏龍蛇”的內(nèi)涵是什么,而 以前并未有人對其有具體的解釋。我以為所謂“赤手搏龍蛇”是指泰州學(xué) 派的學(xué)者大都不受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限制,只憑自我之體悟而對經(jīng)典進(jìn)行隨意發(fā) 揮詮釋,并以此來立身行事,故往往輕視經(jīng)典,蔑視權(quán)威。同時(shí),它也指 泰州后學(xué)大都是平民學(xué)者,他們有急于拯救天下的愿望,并以自我的努力 來實(shí)現(xiàn)其理想。這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禮教所規(guī)定的秩序,所以說“非名 教所能羈絡(luò)”。因此,我認(rèn)為從人格心態(tài)上講,泰州學(xué)派的突出特征是: “赤手搏龍蛇”的狂者精神。其具體表現(xiàn)則是“思出其位”的進(jìn)取意識與 守道自尊的獨(dú)立人格。下面便以王艮為例來加以論述并兼及泰州后學(xué)之主 導(dǎo)精神特征。 一、“思出其位”的進(jìn)取意識 王艮(1483—1540),初名銀,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他 是一位頗具傳奇經(jīng)歷的人物,他出身于鹽丁之家,只念過三年書,卻最終 成為名噪一時(shí)的講學(xué)大師。他開創(chuàng)的泰州學(xué)派也成為明代王門后學(xué)中影響 最大的流派之一。其子王襞曾概括其一生為學(xué)經(jīng)歷說:“其始也不由師承, 天挺獨(dú)復(fù),會有悟處,直以圣人自任,律身極峻。其中也見陽明翁而學(xué)猶 純粹,覺待持循之過力也。契良知之傳,工夫易簡,不犯做手而樂,夫天 然率性之妙當(dāng)處受用,通古今于一息,著《樂學(xué)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 處之義,本良知一體之懷,而妙運(yùn)世之則,學(xué)師法乎帝也,而出為帝者師; 學(xué)師法乎天下萬世也,而處為天下萬世師。此龍德正中,而修身見世之矩 與點(diǎn)樂偕童冠之義,非遺世獨(dú)樂者侔,委身屈辱者倫也。皆《大學(xué)》格物 修身立本之言,不襲時(shí)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處然也,是之謂大 成之圣,著《大成歌》。”(《明儒王東崖先生集》卷一,《上昭陽太師李 石翁書》)三個(gè)階段盡管各有側(cè)重,但其中有一點(diǎn)是共同的,那便是強(qiáng)烈的 成圣欲望,從起始的“以圣人自任”,到最終的“明大圣人出處之義”,成 圣可謂貫穿心齋之一生。心齋一生既未出仕為官,又讀書不多,就其身份 而言,他不具備任何成圣的條件,而他偏偏要成圣,這可算是典型的狂者 舉動,亦可謂是出位之思,用現(xiàn)代語言講便是非分之想。然而,王艮竟然 在一定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自我的人生愿望,他生前弟子眾多,巡撫吳悌還曾一 度準(zhǔn)備被將其薦舉給朝廷,言其“縉紳傾仰,遐邇聞名。”(《明儒王心齋 先生遺集》卷五,《疏傳合編》)他死后各地為其所建祭祠有十四處之多, 而萬歷四十二年泰州后學(xué)周汝登,即公然撰文稱心齋為“東海圣人”。(同 上卷四,《續(xù)譜余》補(bǔ)遺)誠如時(shí)人所贊:“先生布衣,榮名盛世,專祠面 食,與國同休,視夫取青紫博名高,死同腐草者,奚啻云泥也?誠無位而 貴,無爵而尊,儼然孔、孟之家法,猗與休哉,行將與俎豆?fàn)庉x也。”(同 上,《萬歷二十三年秋秦州學(xué)訓(xùn)蜀峨眉彭公肖崖梅奠文》)那么,王艮追求 成圣的心理動機(jī)以及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這便是本節(jié)探討的重點(diǎn)。 要解釋王艮求為圣賢的最初動因是相當(dāng)困難的,據(jù)年譜記載,他的家 庭原本比較貧寒,是他在二十歲左右時(shí)因經(jīng)商得宜而家道日漸富裕的。而 正德二年二十五歲時(shí),則是他一生的重要時(shí)刻,本年他“客山東過闕里謁 孔圣及思、孟諸廟,瞻拜感激,奮然有任道之志。歸則日誦《孝經(jīng)》《論 語》《大學(xué)》,置其書袖中,逢人質(zhì)義。”(同上卷三,《年譜》)其弟子 徐樾則對此記載更為具體:“既冠,商于山東,特謁孔廟,即嘆曰:‘夫子 亦人也,我亦人也。’歸即奮然懷尚友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已。” (同上卷四,《譜余》)這種記載應(yīng)該是真實(shí)的,在明代乃至在整個(gè)封建時(shí) 代后期,對孔子的尊崇都是極為隆重的,面對闕里孔廟那古柏參天的肅穆環(huán) 境與拜謁者的虔誠態(tài)度,都會令人對孔子千古不朽的盛名產(chǎn)生羨掩之情甚至 有效法之志,就象當(dāng)年劉邦與項(xiàng)羽見了秦皇帝的赫赫威勢而頓生大丈夫當(dāng) 如是那樣的感覺。只不過作為一般的士人來說,此種感覺只是瞬間性的, 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便會淡忘消失。而王艮卻沒有,他認(rèn)真起來了,回去后即 “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guān)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務(wù)期于有得, 自是有必為圣人之志。”(同上)此種情形發(fā)展到正德六年他二十九歲時(shí), 終于在其意識中有了一個(gè)較為明確的成圣藍(lán)圖:“先生一夕夢天墜壓身, 萬人奔號求救。先生獨(dú)奮臂托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 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徹,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 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住坐語默,皆在覺中。題記壁間。先生夢后書‘正 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于座右。時(shí)三月望夕即先生悟入之始。”(同上)此 處所謂的“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便是“仁”之內(nèi)容,所謂“悟入之始” 也就是由此決定了他求圣的堅(jiān)定不移。這與陽明先生的龍場之悟尚不在一 個(gè)層次,只可以說立定了人生的志向,而并未真正認(rèn)識到自我生命的意義 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實(shí)現(xiàn)自我的人生追求。因?yàn)楸M管此時(shí)王艮為學(xué)已 采取“以經(jīng)證悟,以悟釋經(jīng)”的方法,并得到了“講說經(jīng)書,多發(fā)明自得” (同上)的效果,而且他也具有了“讀書考古,鳴琴雅歌”的自得生活情 調(diào),但直到正德十四年三十七歲時(shí),他所追求的圣人氣象還是相當(dāng)可笑的: “一日喟然嘆曰:‘孟軻有言:言堯之言,行堯之行,不服堯之服可乎?’ 于是按《禮經(jīng)》制五常冠,深衣,縧絰,笏板,行則規(guī)圓矩方,坐則焚香 默識。書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nóng)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 貴賤賢愚,有志愿學(xué)者傳之。”(同上)他雖已立志作圣人,但所重視的仍 是表層的形式,如他這般古服古行,適足被周圍人視為荒唐古怪,而張惶 于外的事實(shí)也說明其內(nèi)心對圣學(xué)尚無深刻之解悟。此猶如當(dāng)時(shí)的前七子, 雖立志興復(fù)詩文之古道,卻只注重形式的古色古香,從而難以取得真正的 實(shí)效。但本段人生經(jīng)歷對心齋本人來說依然意義重大,因?yàn)樗吘箾Q定了 其一生的人生志向,并通過對經(jīng)典的初步學(xué)習(xí)體悟而提升了自我的人生境 界,起碼在主觀上完成了做一個(gè)教化萬民的圣者的心理準(zhǔn)備。總結(jié)王艮此 一段的為學(xué)經(jīng)過,可以說是謁孔引起了他成圣的念頭,并始終堅(jiān)持不懈。 但謁孔只是一個(gè)外部誘因,則作為心齋的主觀內(nèi)因又是什么呢?許多人都 指出了他的平民身分與未染俗學(xué)的重要作用,徐樾認(rèn)為王艮之所以能“師 心自悟,見其大者”,“蓋先生生長海隅,無紛華世味之染,又少不為俗學(xué), 無言語文字之障,其得天全矣。”(同上卷四,《續(xù)譜余》)有人問鄒元標(biāo): “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他回答說:“惟 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同上)這種說法當(dāng)然是有道理的, 由于他沒有從事科舉文章的學(xué)習(xí),所以少了那點(diǎn)富貴功名的念頭,同時(shí)也 更少傳統(tǒng)的負(fù)擔(dān),使其思維未陷入僵化的程度;尤其是他沒有介入官僚的 行列,故而未被限制在各種規(guī)定的禮儀制度中,從而使他有了大膽的想象 力與強(qiáng)烈的自我膨脹意識。當(dāng)然,這種想象力也許各個(gè)時(shí)代都會在某些士 人身上出現(xiàn),但是否能夠發(fā)育長大則要視其所處時(shí)代的整體特征以及合適 的個(gè)人機(jī)緣。王艮是幸運(yùn)的,他不僅處于明代中期士人個(gè)體意識日益滋長 的時(shí)代,更由于他有幸遇到陽明先生這樣的心學(xué)大師,最終方成就了他的 求圣愿望,從而使他沒有停留于形式的張狂而獲得了支撐其圣人意識的理 論內(nèi)涵。 因而,王艮之遭遇陽明先生便成為他人生的又一轉(zhuǎn)折點(diǎn)。他是在一個(gè) 偶然機(jī)會中得知了陽明先生講學(xué)的消息的,當(dāng)時(shí)有一位名叫黃文剛的塾師 在泰州聽到王艮講學(xué),告訴他與江西王都堂所講頗為相類,這引起了王艮 濃厚的興趣,于是他決定前去拜訪,否則也許他會一直在泰州一隅張狂下 去而得不到任何正果。陽明年譜是如此記載正德十五年二王之相遇情景 的: 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zhí)木簡,以二詩為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 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 “老萊子服。”曰:“學(xué)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xué)服其服, 未學(xué)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cè)。及論致知格物,悟曰: “吾人之學(xué),飾情抗節(jié),矯諸外;先生之學(xué),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 遂反服執(zhí)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為“艮”,字以“汝止。”(《王陽明全集》 卷三四,《年譜》二) 此處所言王艮所獻(xiàn)二詩尚存于心齋文集中,其曰:“孤陋愚蒙住海濱, 依書踐履自家新。誰知日日加新力,不覺腔中渾是春。”“聞得坤方布此 春,告違艮地乞斯真。歸仁不憚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專心循上帝, 從違有命任諸君。磋磨第愧無胚樸,請教空空一鄙民。”(《明儒王心齋先 生遺集》卷二,《初謁文成先生詩二首》)他表示了自學(xué)自悟而心有所得的 自信,更有“立志惟希一等人”的成圣愿望,同時(shí)也講出了“去取專心循 上帝”的治學(xué)路徑,所以方會引起陽明先生的興趣。但陽明一眼便看出他 只重形式外表之依仿而缺乏深刻內(nèi)涵的特點(diǎn),而通過近乎禪機(jī)的對話,終 于使王艮認(rèn)識到了自身“飾情抗節(jié)矯諸外”的不足,以及陽明“得之心” 的“精深極微”,從而心悅誠服地執(zhí)弟子禮。當(dāng)然,實(shí)際情形也許并不象 陽明年譜所記載的那般簡捷明快,這不僅是在王艮年譜中還有首日折服而 夜里又悔之的反復(fù),更重要的是二人還有無法調(diào)和的分歧,當(dāng)二人論及“天 下事”時(shí),陽明說:“君子思不出其位。”王艮說:“某草莽匹夫,而堯舜 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陽明說:“舜耕歷山,忻然樂而忘天下。”王 艮說:“當(dāng)時(shí)有堯在上。”(同上卷四,徐樾《心齋別傳》)對于此一是否 要“君子思不出其位”的爭議,后人有不同的評價(jià),有人認(rèn)為“這是王艮和 王守仁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也反映了封建社會中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 的對立。”(侯外廬等《宋明理學(xué)史》下,第424頁)這種說法恐怕是有些 言重了。因?yàn)樵诖硕卧捴螅柮鲗π凝S還有一句“足見所學(xué)”的獎(jiǎng)掖之 語,看來他對王艮立志用世與指責(zé)朝政混亂的話還是予以認(rèn)可的。二人的 分別恐難用階級對立來判定。陽明的確是不贊成思出其位的,這不僅對心 齋是如此,對其他人也是如此,如他有一位無甚功名的弟子童可剛,寫了 一篇《八策》的奏章,自認(rèn)為是“致治垂統(tǒng)之一策”而欲上奏朝廷,然陽 明堅(jiān)決反對,這除卻文中多為“老生常談”外,更重要的是陽明認(rèn)為:“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可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故而他要求 “可剛焚此魔障”,“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jìn)德為務(wù),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王陽明全集》卷二一,《與童可剛 書》)但陽明先生又何嘗不知道朝廷之黑暗與世道之混亂,他又何嘗不想為 重整朝綱而有所作為。但此刻深陷危機(jī)中的陽明非常清楚靠個(gè)人的進(jìn)諫不僅 不會有任何作用,而且還會招來意外的禍患。因此他雖然贊賞心齋精神的可 嘉,卻不同意他去冒這個(gè)沒有任何積極結(jié)果的危險(xiǎn)。但作為偏居鄉(xiāng)野的平民 學(xué)者王艮,卻不可能知曉朝中復(fù)雜的政治形勢與武宗荒唐的嚴(yán)重程度,僅憑 著一腔熱情便要去“堯舜君民”,實(shí)在是很幼稚的。后來他在嘉靖年間給 朋友的信中說:“今聞主上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行,何不陳一言為盡 孝道而安天下之心,使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 卷二,《與南都諸友》)這顯然是針對大禮議中世宗的表現(xiàn)而出的主意,可 以說對此次事件的復(fù)雜性一無所知。故而陽明勸心齋“思不出其位”,固 然有其作為臣子而受封建禮教限制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表現(xiàn)了其政治的 成熟與對王艮的關(guān)心,實(shí)在說不上是“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的對立。” 然而,王艮卻并沒有接受陽明的忠告,反倒更激起了他濟(jì)世的熱情, 據(jù)心齋年譜記載: 一日,入告陽明公曰:“千載絕學(xué),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 聞此學(xué)乎?” 因問孔子當(dāng)時(shí)周流天下,車制何如?陽明公笑而不答。既辭歸,制一 蒲輪,標(biāo)題其上曰:“天下一個(gè)萬物一體。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fā) 愚蒙。遵圣道天地弗違,致良知鬼神莫測。欲同天下人為善,無此招搖做 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作《鰍鱔賦》……。沿 途聚講,直抵京師。……比至都下,先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 文門變?yōu)槿肆ⅰ3科穑壬m至。時(shí)陽明論學(xué)與朱文公異,誦習(xí)文公者, 頗牴牾之。而先生復(fù)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大異。會南野 (歐陽德)諸公在都下,勸先生歸。陽明公亦移書守庵公(心齋之父) 遣人速先生。 先生還會稽,見陽明公。公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 乃及門三日不得見。一日,陽明公送客出,先生長跪曰:“某知過矣!” 陽明公不顧。先生隨入至庭事,復(fù)厲聲曰:“仲尼不為已甚!”于是,陽 明公揖先生起。時(shí)同志在側(cè),亦莫不嘆先生勇于改過。(同上卷三) 按年譜將此事置于嘉靖元年之下,實(shí)誤。據(jù)其他多處記載均為嘉靖二 年,可信。⑦根據(jù)心齋《鰍鱔賦》所表現(xiàn)的思想,仍是典型的儒家社會關(guān) 懷意識,并沒有什么出格的成分,如“吾聞大丈夫以天地為一體,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故而當(dāng)他看到天下百姓象缸中之鱔覆壓纏繞而難以 透氣時(shí),便欲化身為鰍而上下左右松動之,以使之轉(zhuǎn)身通氣而有生意,而 這正是一個(gè)儒者應(yīng)具的情懷。但值得注意的是,心齋不僅要化身為鰍,他 還要“奮身化龍,復(fù)作雷雨”,于是便要“整車束裝,慨然有周流四方之 志”,這便是他在結(jié)尾的詩中所表示的:“一旦春來不自由,遍行天下壯皇 州。有朝物化天人和,麟鳳歸來堯舜秋。”(同上卷二)這就不僅僅是要做 一個(gè)兢兢業(yè)業(yè)的儒家官員或?qū)W者,而是要做拯救天下的圣人了。于是,又 出現(xiàn)了另一個(gè)夢中的意象,即無首的“黃龍”,盡管這一次不是王艮本人 的夢,而是一個(gè)不知姓名的老人的夢,因而在真實(shí)性上或許要大打折扣, 但泰州后學(xué)卻非常重視這個(gè)夢,他們不僅將其鄭重地編入年譜中,而且還 留下了近乎神奇的傳說,萬歷時(shí)的蔡毅中所作心齋傳記說:“將至都門, 有叟夜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yōu)槿肆ⅰ3科鹜颍壬痢[女?br> 其象,與立談,則風(fēng)至冷冷動人。”(同上卷五)非但老叟夢中的黃龍頗具 神性,連現(xiàn)實(shí)中的心齋也籠罩了光環(huán)。此則并無多少根據(jù)的傳說之所以被 泰州后學(xué)如此看重,是因?yàn)樗鼧O具代表性的意象功能:心齋是龍,他想呼 風(fēng)喚雨;可他是無首之龍,是沒有任何官位的平民儒者,故而他的呼風(fēng)喚 雨便是出位之思。用王艮本人的話說這叫“雖不離于物,亦不囿于物”, 他要管人間之事,又不欲受人間之管,這便是他的思路。此一思路不僅體 現(xiàn)在心齋身上,更體現(xiàn)在其后學(xué)顏山農(nóng)、何心隱諸人的身上,從而形成了 泰州學(xué)派思出其位的傳統(tǒng),難怪他們會如此重視無首黃龍的意象了。這種 人生理想在處士橫議的戰(zhàn)國時(shí)期也許方不被人視為怪異,可早在漢代朝廷 已經(jīng)有了“禁游行”的詔令,心齋卻要在千馀年后專制制度空前加強(qiáng)的明 代重溫戰(zhàn)國舊夢,不僅要在民間講學(xué),還要到京場中去教化士人,則在陽 明眼中顯然屬于狂妄之舉了。盡管經(jīng)過陽明先生此次的嚴(yán)厲教訓(xùn),王艮以 后有所收斂,起碼不再奢望著到京城去招搖過市了。但嚴(yán)格說來他終生也 沒有改變這思出其位的意識,比如說他在參與均分草蕩時(shí)說:“裂土封疆, 王者之作也;均分草蕩,裂土之事也。”(同上卷二,《均分草蕩議》) 表面上似乎有些小題大做,其實(shí)是他出位之思的一次實(shí)驗(yàn)。 盡管陽明未能從根本上改變王艮的狂者人格,但他與陽明的遇合仍具 有深遠(yuǎn)的意義,他不僅在陽明那里印證了自己的心悟所得,結(jié)識了諸多的 王門弟子,從而更堅(jiān)定了自我的成圣志向,更重要的是陽明的心學(xué)良知理 論充實(shí)了他的心靈世界,這使他的求圣不再流于外在的狂怪行為,而有了 較成熟的理論闡發(fā),因而也才能成為泰州學(xué)派的宗師。對于二王遇合的重 要意義,泰州后學(xué)是普遍承認(rèn)的,如鄒元標(biāo)說:“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 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證之,宜其為天下師也。”(同上卷四, 《續(xù)譜馀》)此言堪稱精練,正是王艮自身的狂者氣質(zhì)與陽明對他的影響 結(jié)合起來,才成就了心齋本人及其泰州學(xué)派。如果說“出位之思”是心齋 人格心態(tài)的支撐點(diǎn)與泰州學(xué)派的立派根基的話,而陽明良知?jiǎng)t是其不可缺 少的理論助成因素。 |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版權(quán)所有 北京國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