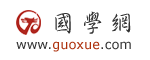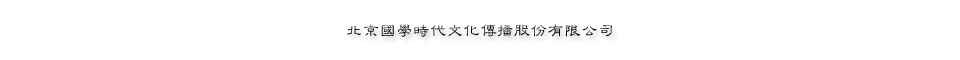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
在時代劇變的同時,中國圍棋也正進行著除舊布新的變革。清末、民初間,正值中國圍棋的傳統“舊法”(置有“座子”的舊式棋法)與“新法”(廢除“座子”的現代棋法)交替的時期。隨著中日棋手之間的接觸交流,在棋界掀起了一股學習日本棋藝的新風。在提高棋藝方面,生活在這一特定時期的中國棋手不僅有與日本棋家交流的機會,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日本棋譜可資借鑒,比單純效法古譜的清末棋手肯定有利得多。所以,民國期間中國圍棋水平比清末有所提高,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出于復雜的社會原因,民國圍棋進步的速度仍相當緩慢。
辛亥革命后,中國資本主義雖然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此時中國人民并未擺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國家也沒有獲得真正的統一。在前后近40年的民國時期,內戰、外戰、大小軍閥混戰蜂起。這樣多變、多難的時局勢必嚴重影響包括圍棋在內的各種文化、藝術的發展。因此,盡管民國棋手已接觸到比較先進的棋理,又對圍棋振興懷有強烈的愿望,然而,處在這樣特定的時代環境中,他們的才智不可能得到充分發揮,舊中國政府也從未為提高圍棋水平創造必要的條件。以下展示的民國棋界狀況,正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經濟收入方面,民國棋手主要靠“賭彩”、“幫彩”與傳授棋藝。這種相沿已久的舊生活“模式”雖然也促使他們比以上層文人為主體的清末棋手重視棋藝進修,但此時民貧國匱,單純以藝謀生,將顯得十分艱難。所以多數棋手仍要兼有它職,才能維持溫飽,一旦時局變化,他們還要為衣食走南串北。由于生活得不到保障,決定了棋手社會地位的低下,也嚴重妨礙了民國圍棋的進步。
民國時期沒有全國性的圍棋組織,也沒有由國家機構創辦的棋社、棋院。重要圍棋交流通常只能在供來客對局的大小茶樓(館、室)與棋會、棋社(包括由地方棋手聯合組織的棋會、棋社,私家舉辦的棋會,棋社)等場所進行。這類茶樓、棋會屬于私家經營,基礎比較薄弱,一旦遇到實際困難,就隨時可能倒閉。但在漫長的舊中國時期,它門就是中國棋手切磋棋藝的基本陣地。
民國年間知名棋手主要聚集在大型城市進行交流。因為大城市不僅是文化、經濟的中心,而且擁有多層次的棋藝愛好者,棋手在這里也有較大的活動余地。可是,知名棋手都走向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棋手就難免囿于見聞,不利于地方圍棋活動的開展。這一現象,直到三十年代后才稍有改觀。但就全國而言,圍棋普及的程度仍十分低下。
民國時期從未舉辦全國性圍棋競賽,以致不同地區的棋手很少有互相交流的機會。到了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地方圍棋組織不斷增多,圍棋活動比較頻繁,開始進行跨越地區的城市之間的圍棋比賽,并有進一步向全國性圍棋競賽發展的趨勢。旋因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各地棋友星散,組織大型比賽自然更無希望。
民國時期出版的圍棋書譜與有關著作種類繁多,大致分編譯日本棋譜、介紹中日交流對局、翻印古譜,以及圍棋筆記、棋話等,涉及面相當廣泛。另外,由于民國時期報刊盛行,為宣傳圍棋提供了方便;少數圍棋組織還出版圍棋定期刊物,受到讀者的歡迎。可是,不論報刊圍棋欄或是定期圍棋刊物,都因社會動蕩,無法長期堅持。
在民國時期,只要時局相對穩定,圍棋活動就呈現上升的趨勢。例如:二十年代前期的北京,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南京,抗戰勝利后的上海等,都曾在短暫的安定環境中涌現許多名手和大小圍棋組織,也冒出一些才能出眾的青少年棋手。足見在廣大群眾中對開展圍棋活動蘊有很高的熱情,民國棋手也為推動圍棋的發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可是,在政治腐朽、民生艱難的舊中國,這樣的“興旺”終究不能長期維持。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國內僅有少數棋手達到專業四段的棋力,與世界先進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第一節 中日圍棋交流
民國建立直至四十年代初期,來訪我國的日本棋手絡繹不絕,其中,除少數屬于旅游性質或在中國僑居外,多數均由我國棋界支持者聘請前來。通過棋藝交流,加深了兩國棋手之間的友誼,也促使中國棋藝不斷提高。據現存資料作不完全統計,除高部道平從1909年至1924年間屢次來訪外,還有十幾位日本棋手來訪。
影響較大的來華訪問有:
1918年,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邀請日本名手廣瀨平治郎(六段)訪北京,廣瀨的弟子巖本薰(初段)亦隨同前來(見日本林裕《大正圍棋史年表》)。翌年,廣瀨與巖本薰又同訪上海,當時上海名手張澹如、潘朗東、吳祥麟等與廣瀨對局被讓3子,與巖本對局被讓先二,可見此時我國圍棋水平仍然低下。
1919年5月,日本瀨越憲作(五段)來青島漫游,因由駐華日本某軍官的介紹,瀨越前往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瀨越在京與中國棋手汪云峰、伊耀卿、顧水如等屢次對局,瀨越歸國后,發表《支那之棋界》,對近代中、日圍棋交流經過,中國棋界支持者與知名棋手,中日圍棋規則的差異均有闡述。此后,瀨越長期留意中國棋界動態,接連發表了《中國棋界之現狀》、《西車南船游記》、《訪問中國》等多篇文字,熱情宣傳中國圍棋的進步。
1919年秋,段祺瑞與當時財政總長王克敏集資聘請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來訪。秀哉到北京后,除與瀨越憲作下了半局表演棋外;其余均下讓子棋。隨后秀哉又應南方名手的邀請,來到上海。這是民國時期日本“名人”唯一的一次來訪。從現存記錄來看,當時中國名手善耆、顧水如、潘朗東、何星叔及段祺瑞等均被秀哉讓3~4子。據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記載,秀哉于9月27日離日本來訪,11月24日歸國。
1920年夏,日本加藤信(五段)來訪上海,南方名手范楚卿、潘朗東、方金題、何星叔、吳祥麟、唐善初、王子晏、劉儼廷、宋懷仁等先后受到他的指點。
1921年春,日本鈴木為次郎(六段)經新加坡來到上海,在張澹如宅居住一月有余與上海棋手張澹如、何星叔、潘朗東、吳祥麟、王子晏、陶審安等廣泛交流。上海名手陶審安奉鈴木為師,經常向他請益。鈴木歸國后,仍與陶繼續書信往來,雙方曾就古代“圍棋十訣”的內容進行反復研討,并試行文字上修飾與訂正(見《東瀛圍棋精華》、《圍棋》)。
二十年代初、中期,日本棋手赤巖嘉平(三段)、安藤馨(三段)、山平壽(四段)、都谷森逸郎(五段)等先后在上海交流。此間,中國王子晏棋力劇增,他與日本棋手對局中獲得很高勝率(見胡沛泉《圍棋紀錄·故王子晏對局自留棋稿總統計》)。??
1926年8月,日本巖本薰(六段)、小杉丁(三段)來訪。8月20日,巖本薰在北京富戶李律閣宅與年僅12歲的中國少年吳泉(清源)對局。吳在初讓3子的條件下戰勝了巖本,改讓2子后,吳少年始以微差致敗。3天后,巖本薰又在李律閣宅讓汪云峰及劉棣懷2子對局,巖本戰勝了汪云峰,但負于劉棣懷。顧水如、王子晏、劉棣懷、吳清源等棋手的涌現,證明中國棋界已逐漸換上了一代新人,巖本薰歸國后,發表《支那漫游記》一文,記述了與中國棋手切磋的實況。???
1927年冬,日本井上孝平(五段)前來北京與此時已有“神童”之譽的吳清源對局,初由井上讓吳清源2子,連弈2局,井上均因形勢被動打掛。于是井上主動提出將棋分改為讓先。繼而再弈3局,雙方1勝、l負、1打掛。井上局后,對吳清源的棋才驚嘆不止,發表感想說:“他(吳)已知道日本人所弈的棋形,而且隱約看出他有改進日本棋形的跡象。”這無疑是對吳少年棋藝才華的高度評價。由于巖本薰、井上孝平等日本棋家歸國后廣泛宣傳,吳清源的才能終于引起中、日棋家的關注。???
1928年9月,日本瀨越憲作派遣他的弟子橋本宇太郎(四段)前來北京,進一步考察吳清源的棋力,結果吳清源執黑2局連勝。同年lO月,在中外友人的協助下,吳清源東遷日本深造,后來終于成長為名滿天下的大國手。??
1929年7月,日本瀨越憲作(七段)、橋本宇太郎(四段)來訪上海,與上海棋手張澹如、吳祥麟、潘朗東、王子晏等切磋棋藝。此間,王子晏執黑對橋本的一局棋弈了3天,費時15小時以上,始以和局告終(見瀨越憲作《西車南船游記》)。???
1930年7月至8月,日本筱原正美(四段)、小杉丁(四段)來訪上海。上海上場棋手有王子晏、潘朗東、劉棣懷、魏海鴻、陳藻藩、張澹如等,陣容相當雄厚。對局雖然均由中國棋手執黑先行,但日雙方競爭激烈,勝負之數往往在毫厘之間,而屢次出現一局棋連弈兩三日的現象,可見中國一流棋手已對日本四段棋手構成威脅(見日本小杉丁、筱原正美《中華棋壇訪問記》)。
1934年5月至7月,日本木谷實(六段)、吳清源(五段)、安永一(日本棋院編集總長、當時四段)、田岡敬一(當時初段)來訪上海、無錫等地。此時木谷與吳清源在日本幾乎家喻戶曉,由他們共同創造的“新布局”風靡一時,對中國棋界也有巨大影響。我國名手顧水如、劉棣懷、魏海鴻、王幼宸、雷溥華、張澹如、張恒甫、沈君遷等先后登場。其中劉棣懷、顧水如曾執黑戰勝安永一,魏海鴻在被讓2子時曾勝木谷實,但在被木谷、吳讓先的對局中全部敗北。這一戰績,證明當時中國棋手尚不具備沖擊日本一流棋家的實力。
1942年10月,日本瀨越憲作(八段)、吳清源(八段)、橋本宇太郎(七段)、井上一郎(四段)一行來訪,曾與上海、南京及北方南下棋手交流。此間正值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尖銳,但懶越一行訪問期間曾向部分中國棋手贈送“段位”,對中國棋界產生了影響(見橋本宇太郎《日華手談》)。
民國時期,原先一直在低谷徘徊的中國圍棋終于擺脫了傳統著法的束縛,提高了藝術境界,這與日本棋手的來訪、指導,以及日本先進圍棋技術的引進,有著緊密的聯系。當然,由于民國時期國情復雜,少數日本戰爭罪犯曾違背人民意志,悍然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都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極其嚴重地破壞了包括棋手在內的兩國人民之間的正常交往。尤其是1937年至1945年間,這是中、日交流史上“只留下流血和破壞的最壞的八年”(引自日本滕加禮之助《中日交流二千年》)。此間,淪陷地區雖然也曾出現以偽政權名義建立的棋院,如1941年在偽“滿洲國”新京(長春)成立的“滿洲棋院”,1943年偽“華北臨時政府”在北京成立“華北棋道院”,以及在青島、鞍山、漢口、開封等地先后設立的“支部”或“俱樂部”,實際上這都是些受日偽操縱的圍棋組織(見日本1942年版《大手合精選·棋界一年》、日本林裕《圍棋百科辭典》等),其目的也不在于宣揚棋道。但從長達兩千年的中日交往史來看,唯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圍棋在增進兩國人民友誼與溝通情感方面,無疑起有積極的作用。圍棋由中國傳向日本,反過來中國棋手又向日本棋手學到很多有益的棋理與知識,這對中國圍棋的發展與圍棋走向世界,都具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