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情”的高度重視是晚明文化的中心內(nèi)容之一,可是我們還遠(yuǎn)遠(yuǎn)不能達(dá)到對情和“情教”理解的共識(shí)。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在現(xiàn)有的對情的各種解釋之外另尋一種新的定義,而是首先承認(rèn)情的多義性,然后考察這種多義性形成的原因,最后再思考情與文、感情與文學(xué)表現(xiàn)之間的關(guān)系。
情之所以意義不定,首先因?yàn)樗c一系列的周邊概念之間的關(guān)系模糊多解。包括“性”、“名”、“理”、“欲”、“禮”、“志”、“陰”、“陽”等的這些概念與情的互動(dòng)從來都是圍繞著對性之善惡問題的爭論,從而造成了情與倫理道德之間關(guān)系的模糊。以“名”為例,它作為道德規(guī)范,其自身內(nèi)在的矛盾,也就是“辨同異”與“明貴賤”之間的不相吻合,在明末清初以寫情為主的才子佳人小說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我們當(dāng)然不能否認(rèn)馮夢龍所倡導(dǎo)的“借男女之真情,發(fā)名教之偽藥”的積極意義,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名教”自身的矛盾分化和由此而來的“情教”的復(fù)雜性。就連馮夢龍自己都明確表示了他的“情教”和倫常的不可分:“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子有情於父,臣有情於君。”
從情與倫理道德之間的糾葛入手,我們可以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到,情的涵義之所以飄渺不可捉摸,是和這個(gè)概念本身作為特殊意義效果的語言載體分不開的。在這一點(diǎn)上,格厄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和房廷(Jacques Fontanille)強(qiáng)調(diào)話語的中介作用的《激情符號(hào)學(xué)》(The
Semiotics of passions)對我們進(jìn)一步理解“情”的概念有很大的啟發(fā)。從情的多義性和語言的關(guān)系出發(fā),我們自然也就聯(lián)想到《文心雕龍》中所提出的“情文”的概念對中國文學(xué)語言中“無情便無文”的特質(zhì)的概括。問題是,我們可不可以進(jìn)一步說“無文便無情”呢?如果堅(jiān)持認(rèn)定“情”即是“性”,是自然生成的,是本質(zhì)的,我們當(dāng)然不能同意“文”是“情”的前提;可是我們?nèi)绻煌浨樗艿亩Y儀的制約、在禮儀的演進(jìn)過程中呈現(xiàn)出來的表演性、人為性,以及情所受的其它道德規(guī)范的制約,我們就不得不承認(rèn)“無文便無情”,文是情必不可少的中介。
“激情符號(hào)學(xué)”對我們的另外一個(gè)重要啟發(fā)是在主客體的關(guān)系問題上。激情或情感之所以發(fā)生,正是由于客體可以以一種價(jià)值的形式,將其自身強(qiáng)加於主體之上,所以由“外感”經(jīng)身體而至“內(nèi)感”的獲得情感意義的過程必須要從客體開始。要理解作為存在、作為語言意義的主體,我們就必須先理解主體所取得的客觀價(jià)值。“激情符號(hào)學(xué)”實(shí)際上就是關(guān)於主體所取得的、失去的、或者懸置的各種價(jià)值。換句話說,情感的發(fā)生不是如笛卡爾(Descartes)等西方啟蒙思想家所說的那樣、由一個(gè)理性的全知的主體積極地在外部世界中取得,而是從客體開始,反方向作用於主體。
荀子說“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其中表達(dá)的主體主動(dòng)尋求的意思是無可置疑的,可是在“求”之前,主體先要判斷什么是“所欲”,也要判斷欲望的對象可不可以得到,這就是取決於客體怎么樣以自身的價(jià)值加於主體之上了。由此看來,“情之所必不免也”難道不是暗示著先由客體而至主體的動(dòng)態(tài)過程嗎?在我們質(zhì)疑西方啟蒙思想所謂全知全能主體的今天,沿著由客體而主體、由它者而自我的方向理解遇物而動(dòng)、遇事而發(fā)的情的發(fā)生機(jī)制,同時(shí)不忘文的中介作用,就不失為脫出非此即彼的詮釋傳統(tǒng)束縛的一條新的思考途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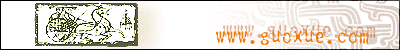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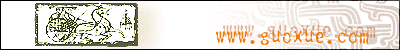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