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以明清之際士人談兵為研究對象,經由對“談兵”這一行為及所談話題的分析,探究士人(“文士”,“文人”)與“兵事”的關系,文臣、文士在軍事事務中的參與及參與方式,以及導致參與的制度條件,討論鼓勵了士人談兵的諸種因素,以至軍事參與對于士人心態、行為方式、自我角色意識的影響。
本文所分析的,是作為文士、文人行為的“談兵”。所謂“文士”、“文人”,前者與武將,武人相對待,后者則指“儒者/學人/文人”類別劃分中的文人類,即士人中主要從事詞章的那一部分。文人談兵,興趣通常在兵謀、方略。本文認為,文人的有關行為在儒學氛圍中,具有某種挑戰性,不妨視為文人的“文化姿態”。
本文將明清之際有關“兵制”的談論也納入了研究視野。明清之際士人的兵制論往往借諸有關“三代”的經典描述而展開,論題在“兵-民”、“文-武”關系上尤為集中。兵民分、合,文武分、合,被作為批評明代兵制、追究明亡原因的重要線索。有關“兵-民”的論說往往圍繞屯政(軍屯)而展開,與“文-武”有關的話題則集中于權力機構中文(臣)武(臣)與軍事有關的職能,與明末軍事中文臣武將的實際關系。擴大了文臣軍事介入的制度性安排,尤其主要出于軍事目的的督、撫之設,以及興起于明代的士人游幕,也可供解釋明代士人談兵的熱情。
本文的分析還及于其他與“兵事”有關的話題,如王夫之對刑法中“徒”、“流”的意義追究,顧炎武關于武裝民眾的主張,吳應箕有末關制科“兼行騎射”的批評。圍繞新型火器的談論也在本文的分析范圍。
明清之際的士人以思想言論的活躍而著稱。即使在本文所涉及的極有限的范圍,這一點也得到了證明。盡管這一時期并未發生大幅度的軍事制度的變革與軍事觀念的更新,士人的有關談論仍然包含了富于深度的文化思考,具有一定的思想史的價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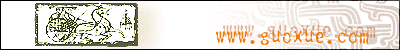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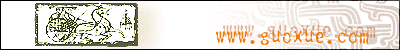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