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筆之分引起過近代以來許多著名學(xué)者的關(guān)注,他們分別對文筆的內(nèi)涵與文筆之分的意義進(jìn)行辨證,結(jié)論卻各不相同。逯欽立認(rèn)為:“近代各學(xué)者文筆的論著,率僅注意于文筆的區(qū)分。他們沒有分期的歷史觀念,對于文筆說的成立,既不曾加以探究,而對于文筆說的演變,又少有討論的,也是游疑其辭,毫無定見。”說學(xué)者們沒有用歷史的發(fā)展的眼光來探究文筆問題,恐難以服眾人之心。然而,學(xué)者們在考察文筆之分時一直有一個文學(xué)與非文學(xué)的成見橫亙在胸中,以為當(dāng)時人已經(jīng)有了純文學(xué)的觀念,于是通過文筆之分來將純文學(xué)獨(dú)立出來。這一成見才是造成文筆問題纏雜不清的根本原因。
我們應(yīng)該把文筆之分放在中國文學(xué)觀念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去考察,盡量排除現(xiàn)代文學(xué)觀念的干擾。孔子揭橥的傳統(tǒng)文學(xué)觀念強(qiáng)調(diào)的是人文教化,它包涵制度和文獻(xiàn)兩個方面。漢武帝獨(dú)尊儒術(shù)以后,儒學(xué)開始僵化,而受楚風(fēng)濡染的辭賦在“潤色鴻業(yè)”的旗號下興盛起來,形成文學(xué)觀念的第一次調(diào)整,即文學(xué)包涵了學(xué)術(shù)(儒學(xué))和文章,由于利祿的引導(dǎo),時人重學(xué)術(shù)而輕文章。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文章的運(yùn)用日益廣泛,文章體裁不斷增加,個人著述蔚然成風(fēng),為了使文章便于歸類,便于稱引,便于學(xué)習(xí),便于評論,文筆之分應(yīng)運(yùn)而生。文筆之分是對文章形式的分類而不是對文章性質(zhì)(是否文學(xué))的分類。當(dāng)時人對文筆的理解并不一致,指稱也有差異。從當(dāng)時的文筆之辨、文學(xué)批評、文學(xué)總集編篡的實際來看,人們其實并不以“文”“筆”作為文學(xué)與非文學(xué)的分野。曹丕《典論·論文》所舉文之四科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陸機(jī)《文賦》所論文之各體包括詩、賦、碑、誄、箴、頌、論、奏、說,劉勰《文心雕龍》“論文敘筆”,所論文體幾乎囊括了當(dāng)時的所有文體,他們都沒有把“筆”排除在文學(xué)的視野之外,而當(dāng)時的文學(xué)選集加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論》、蕭統(tǒng)的《文選》、蕭圓肅的《文海》,均文筆兼收,表明當(dāng)時并沒有今人所謂的純文學(xué)觀念,文筆之分只是他們對紛繁的文體進(jìn)行歸類的一種方式。盡管當(dāng)時人們已經(jīng)意識到當(dāng)下文體的語言風(fēng)格和審美好尚與傳統(tǒng)有別,一部分作者也能比較自覺地追求文學(xué)的抒情性和娛樂性,然而,這只是加強(qiáng)和擴(kuò)張了傳統(tǒng)文學(xué)觀念中對個體感情抒發(fā)和對人的生命狀態(tài)關(guān)注等內(nèi)容,就其整體觀念而言,文學(xué)仍然包涵了文章與學(xué)術(shù),只是人們重文章超過了重學(xué)術(shù),而學(xué)術(shù)已突破儒術(shù)限制涉及諸子百家,文章則更注重情志的抒發(fā)和語言的表達(dá),但其主要功用仍強(qiáng)調(diào)人文教化,即如劉勰所云:“唯文章之用,實經(jīng)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jīng)典。”文筆之分雖然反映出新的文學(xué)因素的成長和傳統(tǒng)文學(xué)觀念的發(fā)展,但純文學(xué)觀念并未產(chǎn)生,中國古代文學(xué)也終于未能走上純文學(xué)的發(fā)展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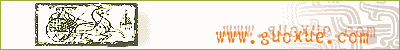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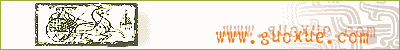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