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師宗強(qiáng)先生在其《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思想史》中,敏銳地捕捉到"南朝重藝術(shù)特質(zhì)的文學(xué)思想傾向",愚弟子再搜尋一些相關(guān)材料,以體會(huì)羅師之卓識(shí)。漢代詩學(xué)體現(xiàn)于《詩經(jīng)》學(xué),其抒情闡釋可以《毛詩大序》為代表;而南朝抒情之特點(diǎn),融入了創(chuàng)作主體空間性地域轉(zhuǎn)移,即作者北南更替的重要因素,此是抒情觀念發(fā)生根本轉(zhuǎn)變之關(guān)鍵。
一、由先秦時(shí)期從個(gè)體之"身"到國家之"事"思想模式來探尋《毛詩序》"抒情"之結(jié)構(gòu)層次。
古人探討問題時(shí),如《毛詩序》的思維方式是:"是以一國之事,系一個(gè)之本,謂之風(fēng)。"而一人之本即"身"直至"心",《周易·系辭下》等往往以身及物,循微見著,由近至遠(yuǎn),由內(nèi)至外,這也是古人之共識(shí),諸子百家莫不習(xí)慣于這樣的思維模式。
二、董理《毛詩序》產(chǎn)生所依附的重精氣養(yǎng)生之歷史文化背景。 養(yǎng)生重乎圖精,這是更深層次的衛(wèi)生要義,而圖精與性情之調(diào)適有緊密的關(guān)系,談?wù)撉樾噪x不開圖精問題。
圖精養(yǎng)生思想尤其突出地表現(xiàn)在齊稷下學(xué)派著作中,如《管子·心術(shù)下》等,似乎在先秦兩漢諸子百家均耳熟能詳,所不同者在于,入世的一派,從此"體"出發(fā),盡量凸現(xiàn)其"用"的一面;而出世的一派,則竭力圖守其"體",防遏觀念的紛亂與法令滋彰。降至漢代,其影響依然深廣。
三、根據(jù)《毛詩序》之政治與文化立場,考察其"抒情"特徵。 《毛詩序》從個(gè)體之心理狀態(tài),窺測國家政治之良窳,無疑是承繼了先秦以來"圖精養(yǎng)生"政治哲學(xué)的思維習(xí)慣。
因此"故變風(fēng)發(fā)乎情,此乎禮義",此"禮義"更有不營擾圖精之衛(wèi)生及人生哲學(xué)層面的含義,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便顯然存在著形成先秦兩漢文藝思想面貌的一個(gè)非國家政治因素,而更偏于養(yǎng)生衛(wèi)生之范疇,必然在漢代影響到文學(xué)抒情觀。
四、文學(xué)抒情觀念在魏晉時(shí)期的演變。 文學(xué)抒情性的逐漸確立,與"文學(xué)自覺"是同步發(fā)展的概念。文學(xué)抒情的發(fā)展,建安時(shí)期可以看作非常重要的一環(huán),然其內(nèi)在動(dòng)因還是由于天人關(guān)系發(fā)生了動(dòng)搖。
承建安文學(xué)思潮之緒馀,抒情于人生之意義,其地位空前上升。降及南朝,曹植輩還顧及的"禮防"更徹底崩塌了,對(duì)此應(yīng)視作南朝士人抒情的新特點(diǎn),兩漢以來圖精養(yǎng)生觀在南朝出現(xiàn)斷裂,這是地域文化差異使然,而此種差異自然要落實(shí)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主體來考察。
五、與圖精養(yǎng)生觀徹底決裂文化背景下的南人之抒情。 這歸根到底應(yīng)從南士儒家經(jīng)學(xué)貧瘠來找原因。南人在文壇凱起,非在深厚的經(jīng)學(xué)氛圍中生長的南人,其人生觀、人格及生活情趣都表現(xiàn)出與北人不同的特點(diǎn),情感恣肆,標(biāo)新立異,更接近于自然本真的生命狀態(tài)。南朝文學(xué)的"抒情",正是在這樣新的文化學(xué)術(shù)背景下展開。
沈約是南人文學(xué)開風(fēng)氣的人物。蕭綱的文學(xué)主張也可一言以蔽之,曰:突出文學(xué)之抒情本體;是宣泄性的,無所顧忌的,他與圖精說完全不同;他是憑藉宣泄,以重建心理平衡,并達(dá)到各種情感的滿足。梁元帝蕭繹文學(xué)觀與蕭觀大致相同,圖精之禁忌,至此一變而成為內(nèi)心之享受。蕭子顯講"委自在機(jī)"與"獨(dú)中胸懷",抒情便成為文學(xué)真生命之所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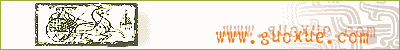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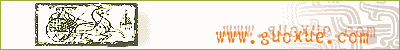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