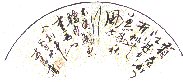內(nèi)容提要:阮籍早年尚志,但是由于遭到政治的昏暗,他無心入仕,只用隱諱的詩文,用放誕不羈的行為來表達自己的反抗。在中國歷史上,像阮籍一樣的人很多,他們多是中國的文人。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他們有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避儒就道成為他們身處亂世的選擇。但這是一種消極的反抗,無濟于事,中國文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脫離了真正的反抗力量——勞動階級,這種階級局限性直到后來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中國革命的時期才被克服。
關(guān)鍵詞:阮籍;亂世文人;反抗;勞動階級
一、在中國歷史上,阮籍是以放蕩不羈著稱的。但是作為一個文人,他并非起初就如此的。
從其家世來看,阮籍的父親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才華出眾,而又有種傲然的風骨,很得曹操賞識。雖然早年喪父,但阮籍還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他“十四、五歲的時候即以勤奮好學、不慕虛榮、道德高尚的古代賢者——顏回、閩子賽為效法的榜樣,刻苦攻讀《書》、《詩》,學習儒家有關(guān)修身養(yǎng)性和治國平天下的種種道理。”〔1〕飽讀詩書的阮籍在文學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詣,許多流傳至今的詩篇就是最好的證明;他還喜愛擊劍,并經(jīng)常練習,劍術(shù)達到了較為精湛的程度,在其《詠懷詩》第四十七首中他這樣寫道:
少年學擊劍,妙伎過曲成。英風接云霓,超世發(fā)奇聲。
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坷。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
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2〕
不僅如此,在修身養(yǎng)性方面他也堪稱一流。
在那個年代,科舉制尚未創(chuàng)立,想要進入仕途多是靠“進入國子學讀書,身懷一技之長,得父輩恩蔭”〔3〕,但要想真正得到朝廷的重視還是需要通過察舉和征辟。于是,“名,成了入仕的最大資本。”〔4〕文采,劍術(shù),涵養(yǎng),有了這些,便有了名,有了入仕得到重用的資本。
阮籍的青少年時期是在曹魏政權(quán)處于強勢的時候度過的,在當時士人積極奮發(fā)精神的影響下,又因著父輩與曹氏家族的感情,他的建功立業(yè)之心已是非常強烈。“嘗登廣武,觀楚漢戰(zhàn)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5〕然而,等到阮籍真正到了可以踏上仕途實現(xiàn)自己多年宏愿的年齡時,社會的政治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齊王曹芳年幼執(zhí)政,實際大權(quán)落在了掌管軍隊的司馬氏父子手中,曹魏中央政權(quán)逐漸式微。此后對皇位覬覦已久的司馬氏集團就開始了篡權(quán)的計劃,政治也隨之走向了黑暗。正始十年司馬懿制造“高平陵事件”,“著名士人何宴等人并受誅戮,史稱此次誅戮‘天下名士去其半'”。〔6〕“高平陵事件”之后,他們的真面目終于公諸于世,為了遮掩自己的丑陋行徑,拉攏當時的名士成為他們的一種重要手段,如若不與之合作,則以武力鎮(zhèn)壓,正始名士的悲慘命運便由此開始。
統(tǒng)治階級在政治上的殘酷斗爭無疑將整個社會推入了黑暗的深淵,文人這一敏感的特定階層在面臨這一殘酷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其建功立業(yè)的機會和期望不但被剝奪,而且,其政治信念和倫理理想也遭到徹底的摧毀更面臨著朝不保夕的性命之憂。在政治高壓下,文人名士或丟命保節(jié),或丟節(jié)保命,而阮籍大概是兩者都不愿丟,他想活著,想干干凈凈地活著,但是聲名威望已經(jīng)讓他走進了司馬氏父子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他難以逃脫。裝作糊涂,逾越常規(guī)也許是他最好的選擇,于是,早年積極入仕之心已蕩然無存,他走上了放蕩不羈之路。對于司馬氏強塞給的官職,如果真的推托不掉,就上任敷衍了事。不論是否為官,他都是終日飲酒,爛醉如泥,或駕車縱行,途窮慟哭而返。清醒的時候吟詩作賦成為他寄托理想,抒發(fā)悲憤的最好辦法。《詠懷詩》中的不少篇章都是這種心情的流露,如第二十二首:
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
修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
葛蕾延幽谷,綿綿瓜瓞生。
樂極消性靈,哀深傷人情。
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7〕
可以看出,悲憤失意的阮籍對“太清”之境充滿了向往。
二、歷史上像阮籍一樣的人很多,他只是中國古代亂世文人的一個縮影。
幽蘭、修竹,這些意象在中國古詩詞中出現(xiàn)得太多了,以此為喻表達悲憤之情的詩篇在《全唐詩》中稍微一翻就能找到不少,中國歷史上像阮籍一樣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們因為仕途失意而縱情于酒,吟詩作畫,回歸田園。陶淵明看不慣官場的相互傾軋,一首《歸園田居》讓后人為之折服;杜牧、李商隱、張祜、許渾、趙嘏等一大批晚唐詩人無奈盛唐的氣象已去,國勢日趨衰微,面對現(xiàn)實,他們自感無力,只在悲苦的詠嘆中過完余生,杜牧也成為沉溺于青樓妓館的名人。“元四家”之中的著名畫家王蒙生活在元朝走向滅亡的時候,社會的動蕩粉碎了他原本美好的夢,沒有了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他也就失去了施展自己才能的舞臺,于是,歸隱山林也就成為他的繪畫作品的主題。
探究這些人的生活背景,他們和阮籍有著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他們早年就受到積極入仕風氣的影響,飽讀儒家經(jīng)典,只待一朝能夠施展自己的才華。然而世事并不如愿,治世與亂世在古代社會總是頻繁交替的。在亂世,社會上更容易上演一幕幕丑劇;在亂世,很多時候靠的是力量,而非正義與否,就像司馬氏集團與曹魏政權(quán)的斗爭,就像正始文人與司馬氏集團的斗爭。手無寸鐵的文人與普通百姓似乎沒有什么兩樣,如果說有區(qū)別,他們也許只有更多壯志未酬的悲憤。在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下,中國文人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自己的理想,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自己的座右銘。他們正是這樣做的,在政治昏暗時,他們不與世人同流合污,保持著自己的高潔。既然仕途已無路可走,他們只有撫平自己激昂澎湃的心,慢慢靜下來,回避骯臟的現(xiàn)實,在云深林密的山中抒發(fā)內(nèi)心的愁苦。歸隱,不管是隱于朝中還是歸于山林,都與道家的思想主旨相契合,在亂世,在政治昏暗的時候,避儒就道作為一種精神,被納入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體系,為悲苦憂憤的知識分子打開了另一條出路。
出淤泥而不染,這種精神歷來是為世人所贊頌的,在越來越高的贊頌聲中,遭遇仕途挫折的知識分子也就很容易以先賢為榜樣,走上避儒就道的道路。面對現(xiàn)實社會的黑暗,面對統(tǒng)治階級的殘暴或腐朽,他們無力反抗,只有苦苦守著已經(jīng)破碎的夢,眼睜睜地看著無道的君主或是險惡的小人禍國殃民;或者說他們有過反抗,以辭官不做或是含沙射影的詩文來反抗。但不管怎么樣,其結(jié)果總是一致的,在政治昏暗的時期,知識分子似乎沒有力挽狂瀾的能力。
作為一代的文人名士,他們是思想界的領(lǐng)袖,但是當人們的思想陷入混亂的時候,他們卻沒有起到積極的能動作用。他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和強大的統(tǒng)治集團公開對抗,即使是現(xiàn)代許多人也認為“他(阮籍)無力承擔重整乾坤的重任”〔8〕。撥開世人對他們的稱贊,我漸漸地對這種處世的態(tài)度產(chǎn)生了懷疑。
三、在筆者看來,阮籍以及中國其他文人的反抗是消極的,無濟于事的。究其原因,便在于他們脫離了最有反抗力量的階級——勞動階級。
阮籍是想通過自己對做官的敷衍了事,以及種種怪誕的行為來表達自己內(nèi)心的反抗,還有更多的人托物言志,寄托對現(xiàn)實的不滿,但實際又怎樣呢?阻礙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腐朽政權(quán)體系仍在繼續(xù),最后發(fā)展到一個極端的時候,有人出來反抗,推翻這個政權(quán)的仍舊不是這些文人,他們甚至在別的力量已經(jīng)開始反抗行動的時候仍無動于衷,“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鎮(zhèn)東將軍毋丘儉和揚州刺史文欽起兵討伐司馬師。……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鎮(zhèn)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琳,并連吳起兵,再次掀起反對司馬氏集團的浪潮。”〔9〕在史料中,沒有一點關(guān)于阮籍等文人支持支持這些起義的記載,雖然這些起義都以失敗告終,但是可以想見,作為士人的領(lǐng)袖,如果阮籍等人起來振臂高呼,號召大家對這些行動進行支持,天下士人必然會云集響應,這將會對司馬氏集團帶來重大的打擊。
但是歷史不能假設(shè),中國古代文人也不會有那樣的意識。縱觀中國社會歷朝歷代起來反抗的力量:“李淵出身于關(guān)隴貴族,任隋太原留守。”趙匡胤原為“后周禁軍統(tǒng)帥殿前督點檢”。朱元璋曾“參加郭子儀的紅巾軍起義”,〔10〕并逐漸擁有軍權(quán)。這些人無一出身于中國的士階層,為什么?為什么中國的文人士子不能起來反抗并取得成功呢?為什么他們會低估自己的能力讓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愿落空呢?關(guān)于這一點,人們多是從他們的忠君思想去分析,認為他們把自己放在了歷史的配角地位,他們愿意以一位賢明的君主為依托,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這種分析我是贊同的,但我認為這其中還有別的原因,就是士階層的階級局限性使得他們沒有看到真正的反抗力量在何處,因此他們也不會發(fā)動這些力量。
也許他們不會想到,反抗的真正力量就是他們眼中所謂的“粗人”:勞動階級。士人當中當然也不乏在為官時“為民請命”的人,但是由于受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思想的影響,他們的努力是為了鞏固皇權(quán),是對朝廷知遇之恩的回報。總體來看,一心想著步入仕途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這些“粗人”走得太遠了。在蘇東坡的《石鐘山記》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如果士大夫和漁工水師能夠很好地溝通的話,二者的互補不是可以很容易破譯石鐘山的秘密了嗎,而事實卻絕非如此。于是我們可以想見,在那個時代士大夫和普通勞動者之間的溝壑有多么的深!即便是虎門銷煙的民族英雄林則徐也接受了清政府讓他鎮(zhèn)壓廣西農(nóng)民起義的命令(幸好他死在了赴任途中,否則后世對他的評價或許就改變了。)。所以說,士階層不會看到下層勞動人民的力量。他們只會像阮籍一樣,胸中塊壘難以排遣,用放誕不羈的行為,用詩酒遮遮掩掩地表達反抗的情緒。或者因為性格不同,像嵇康那樣引頸相向,慷慨壯烈。但是正如魯迅所主張的,不要做無謂的流血犧牲。嵇康倒下了,卻擋不住司馬氏集團篡奪皇位的車輪。制造“天下名士去其半”的慘劇,司馬氏父子甚至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在他們眼里,在軍權(quán)面前,士階層不過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卒,不過是一顆小小的棋子。
是的,士階層自身是弱小的,他們不能獨自承擔拯救國家的重任。只有與下層民眾下結(jié)合,實現(xiàn)先進的思想與堅實的力量相結(jié)合的局面才能讓重整山河的夢變成現(xiàn)實。但是直到近代中國的資產(chǎn)階級都仍舊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由于脫離了人民群眾,革命沒有強大的后盾力量做保障,這也成為最終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的原因之一。即便是中國共產(chǎn)黨,也是經(jīng)過一番迂回之后才找到了中國革命的真正動力。而且,我認為許多中共的領(lǐng)袖人物也是出身于文人的,比如毛澤東,他早年也是熟讀了儒家經(jīng)典的,頗有些“書生意氣”,但是他認識到了“槍桿子里出政權(quán)”,并且提出了發(fā)動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理論。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經(jīng)過黨的感召和教育,四萬多知識分子奔赴了延安,這里以其中的杰出代表范文瀾為例,“他本是一介書生,……‘七七事變'發(fā)生的時候,范文瀾在河南大學任教。他立刻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浪潮中。”〔11〕范文瀾早年投身于“五卅運動”,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40年1月到延安后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史學研究,“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12〕。
試想,如果這一時期的文人仍舊僅僅為了保全自己的名節(jié)而避儒就道,放誕不羈,歸隱山林,那么誰來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如果他們都把自己放在一個高高的位子上,繼續(xù)脫離廣大的勞動階級,那么中國革命什么時候才能成功?所以,正是知識分子克服了這種階級局限性,成為人民當中的一員,才扭轉(zhuǎn)了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的局面。
參考文獻:
[1]田文棠.阮籍評傳——慷慨任氣的一生.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
[2]趙劍敏.竹林七賢.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3]徐公持.阮籍與嵇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劉連德,劉洛.中國古代文人“懷才不遇”情結(jié)的歷史文化成因.安康師專學報,2005,17(6):53-55
[5]劉宏鳳,高建新.阮籍:暗夜里痛苦掙扎的獨行者.內(nèi)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37(2):49-53.
[6]李燕,童坤.從內(nèi)心的孤寂到人格的超俗——阮籍詩文特色的形成.安徽文學,2003,3:39-40.
[7]李世安.從中西比較的角度看儒家文化中的人權(quán)思想.史學理論研究,2004,3:29-35.
[8]程美東.抗日戰(zhàn)爭中的中國文人——以胡適、周作人、陳寅恪、范文瀾為例.百年潮,2005,10:46-50.
[9]江琴.論中國古代文人的悲情自我認同.學習月刊,2006,12(下):27-28.
[10]劉加洪.阮籍反禮教悲劇初探.新疆石油教育學院學報,2005,8(5):109-112.
[11]魏晉風尚和隱士文化.
注釋:
〔1〕田文棠.阮籍評傳——慷慨任氣的一生.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13.
〔2〕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336.
〔3〕趙劍敏.竹林七賢.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89.
〔4〕同上
〔5〕房玄齡等傳.晉書·阮籍傳.中華書局,1974:1361.
〔6〕李燕,童坤.從內(nèi)心的孤寂到人格的超俗——阮籍詩文特色的形成.安徽文學,2003,3:39-40.
〔7〕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365.
〔8〕劉宏鳳,高建新.阮籍:暗夜里痛苦掙扎的獨行者.內(nèi)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37(2):49-53.
〔9〕田文棠.阮籍評傳——慷慨任氣的一生.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32.
〔10〕安作璋.中國史簡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239,305,361.
〔11〕程美東.抗日戰(zhàn)爭中的中國文人——以胡適、周作人、陳寅恪、范文瀾為例.百年潮,2005,10:46-50.
〔12〕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