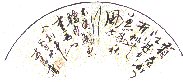近日,由李象潤、李靖莉編著的《濱州歷史與民俗文化考略》一書與讀者見面了。這部旨在“把濱州的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的研究保護和宣傳振興,推向科學(xué)化的建設(shè)和全面繁榮的新軌道”(《后記》)的著作,開拓了當代中國區(qū)域文化研究的新疆域,尤其是其從經(jīng)典到一般、從現(xiàn)實到浪漫、從陳列到敘述的治學(xué)路徑與編著體例,對于區(qū)域文化學(xué)界,“可以轉(zhuǎn)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陳寅恪《 王靜安 先生遺書序》)。
一、從經(jīng)典到一般:歷史與民俗的雙重變奏
當代思想史家葛兆光在其名山之作《中國思想史》中以“一般思想史”取代“經(jīng)典思想史”的嘗試,博得了海內(nèi)外漢學(xué)界的一片喝彩。葛兆光此舉發(fā)端于其“在過去思想史的‘背景'與‘焦點'之間,加上一層‘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也許思想史會更清楚些、更真實些”(葛兆光《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歷史思想史的寫法之一》)的信念。從經(jīng)典到一般的學(xué)術(shù)理路,不僅適用于思想史研究,對于當前人文科學(xué)各個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進程都具有普遍的指導(dǎo)意義。
在這種學(xué)術(shù)思潮下,《考略》一書的橫空出世既是“得風氣之先”的,又是呼之欲出、眾望所歸的。對于區(qū)域文化的研究而言,將歷史與民俗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無疑是“黃金搭檔”,本書的嘗試代表了國內(nèi)區(qū)域文化研究的先覺。著名文化專家、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主席馮驥才在聽取編著們的匯報后,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稱“這在全國開創(chuàng)了歷史與民俗文化研究學(xué)科建設(shè)的新方向,值得在全國推廣”(《后記》)。以民俗之手去觸摸歷史,具有“共時性”的民俗將幫助我們逼近歷史的真實,打破“經(jīng)典歷史”的艱澀古板,還原“一般歷史”的生動活潑;從歷史的視角看民俗,具有“歷時性”的歷史將為我們呈現(xiàn)出一幅以先民的生生不息為題材的波瀾壯闊的畫卷。在橫向上,民俗書寫著歷史中最富情調(diào)的篇章,具有一種“民間靈氣”(馮驥才《民間靈氣》)的力量;在縱向上,歷史觀照著民俗,賦予民間文化以虎虎生氣,塑造了并且鞏固著其中的精神內(nèi)核。歷史與民俗的縱橫捭闔、水乳相融滋養(yǎng)了區(qū)域文化的百花園。然而,長期以來能夠?qū)烧卟⑴e研究的學(xué)術(shù)成果卻是鳳毛麟角。《考略》一書雅集數(shù)十位黃河三角洲文化研究領(lǐng)域的精英于一堂,推杯換盞,觥籌交錯,暢飲歷史文化與民俗的文化的佳釀,描繪出了“經(jīng)典濱州史”的心電圖和脈絡(luò)圖——“一般濱州史”,填補了區(qū)域文化研究的空白,堪稱大手筆和大制作。
在《考略》中,張金路的《孫子兵學(xué)思想的民間考察》和吳名崗的《表現(xiàn)古代戰(zhàn)爭的魯北大秧歌》,表現(xiàn)了在作為孫子故里的濱州,尚武精神及其衍生出的尊賢尚功、奮發(fā)有為的區(qū)域文化精神一脈相承。作為“經(jīng)典”的《孫子兵法》與位居“一般”的民間風俗交相輝映。書中此類文章還有不少,李靖莉、王萍的《黃河三角洲鹽業(yè)生產(chǎn)史考》和孫錫恩的《鹽業(yè)生產(chǎn)史話》從鹽業(yè)生產(chǎn)的角度窺見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讀者從中不難真切地感受到一種活在歷史的快意。與諸多區(qū)域文化研究著作相比,《考略》所提供的柳暗花明、撥霧見真的閱讀體驗彌足珍貴和引人入勝。
二、從現(xiàn)實到浪漫:求證與假設(shè)的有機互動
與學(xué)院派相比,民間學(xué)者的最大優(yōu)勢是善于打通學(xué)科之間的壁壘,獲得一種整體性的觀感。《考略》一書的突出特色便是熔鑄了學(xué)院派和民間學(xué)者的思想精華于一爐,既體現(xiàn)出了一種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又在更廣闊的天地間激蕩著一股學(xué)術(shù)真氣。這種真氣絕非虛無縹緲、瞞天過海,而是根植于古今兼容的“通才”襟懷和中外并包的“雜家”視野。國學(xué)大師黃侃以“博而能一”(黃侃《黃侃國學(xué)講義錄》)四字揭示的治學(xué)真諦,在《考略》一書中得到了忠實地傳承。
當代學(xué)者錢理群提出“以浪漫主義反對爬行現(xiàn)實主義”(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對于推進人文學(xué)科的建設(shè)具有重要的昭示意義。縱觀二十世紀學(xué)術(shù)史,王國維天才般地“古史新證”,陳寅恪奇跡般地“以詩證史”,都令后學(xué)嘆為觀止。他們身上體現(xiàn)出的這種“浪漫主義”的學(xué)風,倒置胡適的名言恰好可以做出詮釋,即“小心求證,大膽假設(shè)”。由于教育體制的原因,時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如此“浪漫”的學(xué)風已經(jīng)幾乎在學(xué)院派的著作中絕跡;進入九十年代,此種狀況雖有改觀,但從學(xué)院的高墻內(nèi)迸發(fā)出的音符的大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望洋興嘆”。然而,民間的“學(xué)術(shù)票友”們此時正以舍我其誰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高漲的建設(shè)熱情、強烈的問題意識、跳躍性和發(fā)散式的思維架構(gòu)以及“十年磨一劍”的扎實學(xué)風對諸多困擾學(xué)界已久的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套用梁啟超的話說,他們的成績“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梁啟超《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考略》的主要編著者之一李象潤,便是他們中的核心成員。
《考略》中輯錄了李象潤的五篇文章,上古濱州史是他最關(guān)心也是成績最為卓著的研究領(lǐng)域。他在濟南大學(xué)徐北文先生大舜研究的基礎(chǔ)上,利用復(fù)旦大學(xué)著名歷史地理學(xué)家譚其驤教授的主要觀點和方法(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出現(xiàn)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將徐北文生前懸而未決的大舜“陶河濱”原址鎖定在了濱州(《昔大舜“陶河濱”原址考——濱州是遠古歷史地理文化考》);進而在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的指導(dǎo)下,他通過考釋周公鼎銘文,為濱州找到了最初的文字記載——“甫古”(即傳世文獻中的“蒲姑”和“薄姑”),并“以小見大”地寫就了東夷興衰史,同時他借鑒北京大學(xué)侯仁之教授以“薊丘”作為突破口研究北京史的經(jīng)驗(侯仁之《關(guān)于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從“營丘”入手,打通了太公封齊前后的歷史,完成了屬于濱州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齊國建都濱州210年考——詮釋西周初年姜太公立國營丘之謎》)。每一步探索都是在“小心求證”的前提下做出的“大膽假設(shè)”,每一次成功都是在“大膽假設(shè)”的基礎(chǔ)上再次進行“小心求證”的結(jié)果。從李象潤身上,從《考略》書的學(xué)術(shù)成果中,可以窺測出其“浪漫主義”學(xué)風的發(fā)榮滋長和蔚為大觀。
三、由陳列到敘述:熱烈與深沉的“重寫”嘗試
上世紀八十年代陳思和、王曉明提出的“重寫文學(xué)史”和九十年代李學(xué)勤提出的“重寫學(xué)術(shù)史”都曾是學(xué)術(shù)界內(nèi)振聾發(fā)聵的聲音。在“重寫歷史”的大潮下,“重寫地方史”成為落在區(qū)域文化研究者們肩上的義不容辭的使命與責任。《考略》無疑可以視作一種“重寫濱州史”乃至“重寫地方史”的有益嘗試。
山東大學(xué)鄭杰文先生在書中論定:“一般來講,邊緣文化在先進性與早熟性方面往往不及中央文化,但黃河三角洲文化卻時時表現(xiàn)出某種先進性和早熟性。”(《黃河三角洲文化的歷史進程及基本特征》)既然如此,“重寫濱州史”便在“重寫地方史”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標志意義。《考略》的編著者們選取了將熱烈的民俗考察與深沉的歷史考釋相結(jié)合的道路,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從陳列走向敘述,提升了編著體例的文本境界,使得全書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論文集的概念,形成了渾然天成的編著風格。
《考略》以黃河源頭沱沱河的洪荒景象作為封面,以現(xiàn)代濱州的民俗風情作為封底,從古至今,一路走來。閱讀全書,似讀萬卷書,更似行萬里路。“該書從選篇布局到裝禎設(shè)計都獨具匠心,書法、篆刻、圖版點綴其間,尤其通過選錄的古詩詞賦,溝通古今,蔚為大觀。”(《前言》)全書分為“綜論”、“歷史”、“人物”、“民俗”和“附錄”五大篇章,各有側(cè)重,亦不乏相互照應(yīng),對濱州歷史與民俗文化精神實質(zhì)的探索貫穿始終。這種精神實質(zhì)是孕育了中華民族的黃河在浩蕩入海時展現(xiàn)出來的勃勃生機,這種探索是站在超時代和跨文化的制高點上以嶄新的和宏觀的學(xué)術(shù)視角對濱州區(qū)域文化進行的“正本清源”式的重新審視。作者們在對“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于其間產(chǎn)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一曰世界觀”(梁啟超《論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的認識過程中達成了高度的一致,因此他們不同的筆風不僅沒有使全書顯得駁雜錯亂、支離破碎,反而為敘述的方式創(chuàng)造出了盡可能多的可能性,百川歸海,共同服務(wù)于“重寫濱州史”的主旨。由此,也不難看出編著者們的用心良苦。
誠然,作為一部嘗試之作,《考略》不乏稚嫩之處。但是,編著者們所做出的開拓區(qū)域文化研究的新疆域的杰出貢獻必將彪炳史冊。鐘敬文先生曾經(jīng)預(yù)測:“歷史學(xué)與民俗學(xué)的交叉研究,正在形成一種趨勢”。(鐘敬文《略談歷史學(xué)與民俗學(xué)的合作研究——晁福林著〈先秦民俗史〉序》)我們希望,濱州歷史與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們以及當代中國區(qū)域文化的研究者們能夠“得預(yù)于此潮流”(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攜手迎來區(qū)域文化學(xué)界的春天碩果。
(《濱州歷史與民俗文化考略》,李象潤、李靖莉編著,黃河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