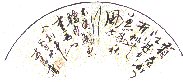緒言
儒學(xué)始于周公,成于孔子,拓于孟荀,凝于漢儒,自此而擬定儒學(xué)之內(nèi)容與形態(tài):自內(nèi)容上說(shuō),儒學(xué)有內(nèi)圣之學(xué)(道德心性學(xué))與外王之學(xué)(政治實(shí)踐學(xué))兩面;自形態(tài)上說(shuō),儒學(xué)有理論儒學(xué)與制度儒學(xué)兩種,理論儒學(xué)中又可分子學(xué)形態(tài)之儒學(xué)與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之儒學(xué)兩類。兩漢三國(guó)以降,儒學(xué)在內(nèi)容上難有新的創(chuàng)造,在形態(tài)上也純?yōu)楣盼慕?jīng)學(xué)和制度儒學(xué),幾百年下來(lái),儒學(xué)乃僵化為一腐朽之工具:古文經(jīng)學(xué)意識(shí)形態(tài)化,制度儒學(xué)亦失去對(duì)社會(huì)秩序之改良和融攝。于是到五代之時(shí),不僅國(guó)家社會(huì)遭受一前所未有之大混亂,而人的道德也沉淪至毫無(wú)廉恥之地步,儒學(xué)亦只能靠斯文敗類如馮道輩所刊刻的幾本書(shū)以綿綿若存。此種種惡相,宋儒不能不深切感受而寓思以解決之:于是,周、邵、張三子以西漢今文經(jīng)學(xué)之天人宇宙觀思想為模型,建立天道觀哲學(xué),以同時(shí)貞定住人倫道德與社會(huì)秩序兩面;二程、朱子深刻而圓融的吸收儒、釋、道三家思想,以更加理性的本體論之天理來(lái)建立內(nèi)圣外王之學(xué)[1];其他如王安石自建一套經(jīng)學(xué)以開(kāi)辟新形態(tài)之制度儒學(xué),陳亮以事功之精神進(jìn)行外王學(xué)之創(chuàng)新,等等;總結(jié)之,即是要以新形態(tài)之理論儒學(xué)重建制度儒學(xué)[2]。然而宋代作為中國(guó)歷史由近古到前近代的重要轉(zhuǎn)變時(shí)期,以上種種舊瓶裝新酒的改良都不能真正開(kāi)出一條全新的思路來(lái),真正開(kāi)啟這條思路的是陸象山。
一、從經(jīng)學(xué)儒學(xué)到子學(xué)儒學(xué)
六經(jīng)之說(shuō),起自孔門(mén),至漢代立群經(jīng)博士,乃形成一經(jīng)學(xué)儒學(xué)之形態(tài)。這是一種詮釋學(xué)的儒學(xué),即通過(guò)對(duì)經(jīng)典之解釋來(lái)闡釋儒學(xué)。此中又分今文經(jīng)學(xué)和古文經(jīng)學(xué)兩派。今文經(jīng)學(xué)通過(guò)闡揚(yáng)經(jīng)典中可資利用之思想來(lái)建立自己的理論,古文經(jīng)學(xué)則進(jìn)行字句之訓(xùn)詁以尋求經(jīng)典最真實(shí)的含義。然而,今文經(jīng)學(xué)終究不能脫離經(jīng)典之矩范,古文經(jīng)學(xué)也無(wú)法擺脫詮釋學(xué)原則之困境,結(jié)果,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之儒學(xué)就成了一個(gè)充滿張力的矛盾凝結(jié)體。至宋代,周、邵、張假今文經(jīng)之天人形態(tài)重構(gòu)儒學(xué),二程、朱子承古文經(jīng)之理性精神而立本體論之天理學(xué),王安石獨(dú)建自己之經(jīng)學(xué)體系,如此種種,雖各有創(chuàng)新,然始終不能逃脫經(jīng)學(xué)中固有張力與矛盾之限制。要擺脫它,必須放棄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之儒學(xué),于是,陸象山乃重新回到孔孟時(shí)代,復(fù)興了子學(xué)形態(tài)之儒學(xué)。
所謂子學(xué)形態(tài)之儒學(xué),是指先秦時(shí)期作為諸子學(xué)之一的孔、孟、荀那樣一種充滿活潑氣息和創(chuàng)新精神之儒學(xué),那時(shí)對(duì)待經(jīng)典是如孔子的“《詩(shī)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wú)邪”,和孟子的“《武成》,取其二三而已”的態(tài)度。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住儒學(xué)的主旨,而不會(huì)陷入到經(jīng)學(xué)的矛盾與張力中去。陸象山于是大膽提出“六經(jīng)皆我注腳”的觀點(diǎn),從而一下子點(diǎn)活了在經(jīng)學(xué)之盤(pán)中困走了近千年的儒學(xué)。
陸象山認(rèn)為:
“學(xué)茍知本,六經(jīng)皆我注腳”
這是說(shuō),做學(xué)問(wèn)只要能把根本端緒處明了與把握住,那么,六經(jīng)不過(guò)是對(duì)我的一個(gè)腳注而已。也就是說(shuō),經(jīng)學(xué)不是學(xué)問(wèn)的大端,辨志、明心才是根本的。當(dāng)我們能讓那普遍而超驗(yàn)的道德本心時(shí)時(shí)刻刻發(fā)動(dòng)流行后,六經(jīng)就自然而然的在我的生命之流中融會(huì)貫通了[3]。
“六經(jīng)注我,我注六經(jīng)”
這是說(shuō),六經(jīng)乃是對(duì)古代能發(fā)明本心的圣賢們的各種道德行為之記述以及用此本心對(duì)各種非道德行為之譴責(zé),所以,六經(jīng)只是對(duì)那本心的一個(gè)舉例證明,而我之本心之發(fā)用流行事實(shí)上也是與古圣先賢之本心的和鳴共唱。因此,六經(jīng)與我是互注的關(guān)系,而說(shuō)到底,究竟還是那本心之發(fā)動(dòng)流行的歷史記錄罷了。因此,對(duì)待六經(jīng)并不需采取經(jīng)學(xué)的一味崇拜、字字株守態(tài)度。
“萬(wàn)物皆備于我,只要明理”
這是承孟子對(duì)待經(jīng)典的態(tài)度而言,進(jìn)而推廣到萬(wàn)物。要旨在本心即是理,所以明理即是明本心,本心既明,則萬(wàn)事萬(wàn)物無(wú)不在握,更隍論六經(jīng)了。
如此等等,足見(jiàn)象山對(duì)六經(jīng)采取的是與兩漢隋唐之經(jīng)學(xué)儒學(xué)迥然不同的態(tài)度,而且與宋代其他儒者發(fā)掘經(jīng)典新內(nèi)涵之新經(jīng)學(xué)也相異。可以說(shuō),他已經(jīng)能擺脫經(jīng)學(xué)的窠臼,并采取主體首位的態(tài)度,而不是經(jīng)典首位,這樣,一下子回到了軸心時(shí)代那個(gè)充滿活力的年代。因此,象山給我們展示出了如同先秦諸子般的一系列特征:好辯論、不重視著作、充滿創(chuàng)新精神和高度自信。相應(yīng)的,他的心學(xué)與周、張、程、朱的思想比較起來(lái)也顯得更能鼓動(dòng)人心和更加活潑。
象山雖然自己沒(méi)有明說(shuō)要由經(jīng)學(xué)儒學(xué)走向子學(xué)儒學(xué),但他對(duì)待經(jīng)學(xué)的態(tài)度,卻事實(shí)上開(kāi)啟并已經(jīng)走上了子學(xué)儒學(xué)之路。這條路后來(lái)為王陽(yáng)明及泰州后學(xué)所繼承,但卻因中國(guó)近代思維的整體挫折而委屈為清朝的史學(xué)儒學(xué)一派。直到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這條子學(xué)儒學(xué)的活潑之路才重新被接續(xù)上。
二、從秩序重建到主體呈現(xiàn)
宋儒面臨之最嚴(yán)峻問(wèn)題,就是整個(gè)制度儒學(xué)的崩塌和外王學(xué)的困境,所以,如何重新建構(gòu)秩序化的制度儒學(xué)并開(kāi)拓出更新的外王學(xué),是宋儒關(guān)心之所在。重視歷史,宋儒發(fā)現(xiàn),漢儒及之后那條儒者為帝王臣的路子已經(jīng)走不通,那條路只能使治道淪喪而使家國(guó)天下成為人主肆意之所在。所以他們認(rèn)為,必須重新建立儒者為帝王師的地位,這樣,既能限制帝王之濫權(quán)并輔助其實(shí)行善政,又能使儒家理想中的三代太平之世得以實(shí)現(xiàn)。在這樣一個(gè)共識(shí)下,構(gòu)建新的秩序化國(guó)家和為這個(gè)架構(gòu)確立理論基礎(chǔ),成為了宋儒努力的方向:周、邵、張三子以宇宙論的天道觀哲學(xué)來(lái)確立此秩序,二程、朱子以理性本體論之天理來(lái)更深層次的確立其根基,王安石自創(chuàng)所謂“新學(xué)”以建構(gòu)出制度儒學(xué)。但是這種種的思想?yún)s在一個(gè)基本點(diǎn)受到了制約,這就是中國(guó)歷史政治的雙重權(quán)源,也即是有治道無(wú)政道,最終的決定權(quán)始終在皇帝那里,而圣君難得,所以,無(wú)論何種秩序重建的構(gòu)思,都不能不因?yàn)榉亲灾髦粍?dòng)性和外在化之軟弱性而陷于無(wú)用[4]。這樣一步步的追下來(lái),我們看到,要徹底解決此問(wèn)題,邏輯上必然走向士大夫這一階層的主體意識(shí)與主體集團(tuán)之形成,而在哲學(xué)上,就是個(gè)人主體性之呈現(xiàn),而陸象山,正是走出這第一步的人(總結(jié)歷史上對(duì)主體性的思考,有三條原則最為基本:即對(duì)主體性擁有之肯定,主體性能發(fā)揮作用之肯定,主體性對(duì)自身負(fù)責(zé)之肯定。我們將看到,陸象山對(duì)此三點(diǎn)都有肯認(rèn)與理解)。
在象山時(shí)代,朱子之學(xué)自外在之天理處已經(jīng)將社會(huì)秩序與道德之理打通,但此是外在的通,人自身在其中只處一被動(dòng)的地位,如此之路,只能造成規(guī)范對(duì)人之強(qiáng)制,而這恰恰可能反過(guò)來(lái)抑制儒者對(duì)社會(huì)之評(píng)議,后來(lái)的歷史證明了這點(diǎn)[5]。象山當(dāng)時(shí)深切的感受到朱子學(xué)的這種傾向,所以他在談?wù)撝刃蛑亟ㄉ峡梢耘c朱子互相唱和,但一談到內(nèi)圣學(xué)處便爭(zhēng)論陡起。因?yàn)橄笊街畬W(xué),本質(zhì)上就在確立人之主體性,進(jìn)而由此突出之主體性貞定住道德實(shí)踐與社會(huì)秩序。
陸象山以為:
“人非木石,安得無(wú)心?心于五官最尊大”
這是說(shuō),作為普遍而超驗(yàn)之道德心是超越感觀而涵攝感觀的,而且,并非是某些獨(dú)特的人才有這個(gè)心,而是人人都有這個(gè)心,所以就這個(gè)意思講,圣賢與我并沒(méi)有什么兩樣,在本具的道德基礎(chǔ)上大家都是相同的。這樣,象山就確定了第一點(diǎn)“每個(gè)人都同樣的具有主體性”。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wàn)物皆備于我,有何欠缺”
這是說(shuō),既然已經(jīng)知道圣賢與我在道德本性上沒(méi)有差異,那么,只要我們使自己那本心開(kāi)朗起來(lái),而不被外物熏染,讓它自己主宰自己,亦不需憑借經(jīng)典和法制,就能讓那道德本心時(shí)時(shí)刻刻自然流淌,就與萬(wàn)物萬(wàn)事匯歸一源,我們就獲得了圓滿的道德境界了。這樣,象山就確定了第二點(diǎn)“每個(gè)人都同樣的能合理運(yùn)用自身之主體性。”
“福禍無(wú)不自己求之者,圣賢只道一個(gè)自字煞好”
此處象山講一個(gè)“自”字,因?yàn)榈赖抡f(shuō)到底都來(lái)源于我自己的本心,所以我的一切行為,道德的、不道德的,都只能由我自己負(fù)責(zé)。外在的社會(huì)風(fēng)俗、法律制度、禮儀規(guī)矩,都僅僅是個(gè)注腳而已。這樣,象山又確定了第三點(diǎn)“每個(gè)人都為自己的主體性負(fù)責(zé)”。
“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fēng)”
這是以孔顏樂(lè)處反對(duì)朱子之說(shuō)法,而突出自身之主體性。因?yàn)橄笊骄哂辛饲懊嫠f(shuō)的我有、我能、我負(fù)責(zé)三層主體性理念,所以已經(jīng)無(wú)須朱子的那些格致功夫與天理本體了。既然道德理性之主體已經(jīng)確立,那么,只要此主體自然發(fā)用,就自然能實(shí)踐道德,自然能建構(gòu)秩序,自然能內(nèi)圣外王了。
象山這條通過(guò)呈現(xiàn)主體而重建秩序之路,是一條從根本處入手之路,也因此最難為統(tǒng)治階層所容,只看后世陸學(xué)之低迷與明太祖對(duì)孟子之態(tài)度,就可想見(jiàn)此思路之困頓了。然而真正區(qū)別于秦漢帝國(guó)制度之新社會(huì)秩序與制度儒學(xué)之創(chuàng)建,卻端賴于象山之開(kāi)出主體性之心學(xué)。此條思路,當(dāng)代新儒家和自由主義者開(kāi)始能接契上,但遠(yuǎn)遠(yuǎn)沒(méi)有完成。
三、從近古儒學(xué)到前近代儒學(xué)
中國(guó)之歷史周代以前可算遠(yuǎn)古時(shí)期,有周一代是上古時(shí)期,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是中古時(shí)期,隋唐五代是近古時(shí)期,兩宋至明可算是由近古到近代之過(guò)渡期,可稱之為前近代時(shí)期。此中最明顯之分判,在政治主體之社會(huì)階層的變化:周代中國(guó)之政治主體是貴族,秦漢至南北朝是士族為政治主體,隋唐之政治主體是庶族,自宋代開(kāi)始至明朝則平民成為政治主體是一趨勢(shì),但此趨勢(shì)卻因外族入侵等一系列因素而被延緩到辛亥革命后才得以確立[6]。宋代作為由近古到前近代的轉(zhuǎn)型期,其面臨問(wèn)題之多是中國(guó)歷史上所罕見(jiàn)的,相應(yīng)的,作為對(duì)內(nèi)圣外王有同等關(guān)注的儒家來(lái)講,此時(shí)期所要解決的問(wèn)題也是最多的。也正因如此,儒學(xué)才開(kāi)始復(fù)興,才開(kāi)始能擺脫古代形態(tài),向近代過(guò)渡。在這一過(guò)程中,陸象山的心學(xué)是真正具有過(guò)渡意義的新形態(tài)儒學(xué)之開(kāi)端。
如果說(shuō)周、邵、張三子的天道宇宙論哲學(xué)尚只是對(duì)秩序與道德淪喪的天然反應(yīng),以及在歷史資料中重新發(fā)現(xiàn)資源的舊儒學(xué)再構(gòu)建而已;那么,到程朱時(shí)期,則已經(jīng)開(kāi)始通過(guò)創(chuàng)造新概念來(lái)整合舊有各家學(xué)說(shuō)并試圖豐富和改良儒學(xué),這就是他們的本體論天理哲學(xué)。從某種程度講,以上六子之學(xué)說(shuō)都試圖將之前的所有學(xué)說(shuō)之合理部分都整合到儒學(xué)中來(lái),而朱熹為集其大成者。所以,朱熹從時(shí)間和學(xué)術(shù)形態(tài)上來(lái)看,事實(shí)上是對(duì)古代儒學(xué)之總結(jié)。而到象山這里,一方面他確實(shí)是復(fù)活了孟子之學(xué)的子學(xué)儒學(xué)形態(tài),另一方面,他則從前近代思維的角度對(duì)孟子的道德理性和主體性精神進(jìn)行了十字打開(kāi)的徹底貫穿,從而具有了鮮活的近代氣息。
陸象山認(rèn)為: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所貴乎學(xué)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
這是說(shuō),人之本心與天理是同一的,人要窮理,其實(shí)盡心就是了。這樣一種心學(xué)的講法,表現(xiàn)的是最基本的近代思維——主體理性:人是有巨大的自主性的,人的理性是具有無(wú)窮大的能力的,人通過(guò)對(duì)自己理性的運(yùn)用最終可以達(dá)到對(duì)根本之理的把握。這樣一種近代思維在中西方的前近代時(shí)期都開(kāi)始形成,不過(guò)西方是在知識(shí)方面,中國(guó)則在道德方面。
“在人情、事勢(shì)、物理上做些工夫”,“古人皆是明實(shí)理,做實(shí)事”
這是說(shuō),我們?cè)诰唧w做工夫的時(shí)候,不能再像中、近古時(shí)期那樣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幾部經(jīng)典上,而是要從具體的人情世故入手,體察本心、發(fā)用本心。這樣的精神,蘊(yùn)涵著的是近代思維中的事功精神。象山認(rèn)為,上古圣賢之所以為圣賢,就在于他們能窮人理、實(shí)理、實(shí)學(xué),他的這種認(rèn)識(shí),其實(shí)強(qiáng)調(diào)的是要在具體的實(shí)事中做工夫來(lái)實(shí)踐道德、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
“若某則不識(shí)一個(gè)字,亦須還握堂堂地做個(gè)人”
這是說(shuō),辭章的知曉,考據(jù)的功夫,并不是人的根本,人之根本處在義理,也就是道德理性的本心。從這個(gè)角度講,社會(huì)地位、職業(yè)分途、教育水平,都不應(yīng)當(dāng)造成人的不平等,因?yàn)閺娜酥詾槿说牡赖吕硇陨蟻?lái)說(shuō),人人都是平等的。這樣一種看法,實(shí)際上是近代平民意識(shí)崛起的體現(xiàn),而象山則通過(guò)道德理性之主體將這種平民意識(shí)、平等意識(shí)注入到了儒學(xué)之中。
從上面以及陸象山一生之學(xué)問(wèn)經(jīng)歷來(lái)看,主體理性、事功精神、平民意識(shí),是貫穿其思想的線索。可能他對(duì)自己這些思維的形成,并沒(méi)有完全感受到其時(shí)代意義和巨大創(chuàng)新性。但是,從哲學(xué)思想史和中國(guó)歷史的角度來(lái)看,象山的這些思維確實(shí)是由近古到近代轉(zhuǎn)變中一個(gè)鮮明的轉(zhuǎn)折[7]。象山之心學(xué)為陽(yáng)明所繼承,主體理性和事功精神得到進(jìn)一步的開(kāi)展和實(shí)現(xiàn),而其平民意識(shí)則在泰州學(xué)派中發(fā)揚(yáng)光大。可惜,這種種的近代化儒學(xué)思維都因各種歷史因素之作用而最終在異族統(tǒng)治下喪失殆盡,中國(guó)也終于沒(méi)能憑自己的力量完成由近古到近代之過(guò)渡。所以說(shuō),中國(guó)的前近代歷史是一段最可惋惜的失敗史,而象山的這些具有近代思維特色的儒學(xué)思想也要一直到當(dāng)代新儒家才被重新拾起。
結(jié)論
陸象山之心學(xué),在外在之天理秩序、禮法制度中獨(dú)能見(jiàn)到本性仁義之心,所以他能使凝化傾向嚴(yán)重的程朱學(xué)獲得一活潑之轉(zhuǎn)機(jī),此種轉(zhuǎn)折之完成形態(tài)雖到陽(yáng)明才圓熟,但象山已經(jīng)將其開(kāi)辟豁顯出來(lái)。觀元明兩代官方之推崇程朱學(xué),正是將程朱學(xué)完全凝結(jié)為意識(shí)形態(tài)、社會(huì)秩序、政治制度,這樣一種僵化的思維結(jié)構(gòu)和社會(huì)心理,要到陽(yáng)明及其后學(xué)重張心學(xué),才再次開(kāi)啟了個(gè)性啟蒙之個(gè)體活躍時(shí)代。由此,可知陸象山之學(xué)實(shí)堪稱前近代儒學(xué)思維之開(kāi)端,即儒學(xué)對(duì)近代平民化社會(huì)之適應(yīng),而程朱學(xué)則只能算近古思想之終結(jié)。
總之,陸象山通過(guò)對(duì)道德本心之發(fā)現(xiàn)發(fā)明,擺脫了古代經(jīng)學(xué)思維之束縛,確立了社會(huì)秩序、政治制度的主體性根基,并進(jìn)而形成了其迥異于前賢的突出個(gè)體性的心學(xué)思想。從儒學(xué)史角度看,陸象山是中國(guó)儒者由古代思維轉(zhuǎn)向近代思維之前近代時(shí)期的第一人,他是中國(guó)前近代儒學(xué)之開(kāi)啟者。
參考文獻(xiàn):
1、《陸九淵集》,陸九淵著,中華書(shū)局1980年第一版。
2、《象山語(yǔ)錄·導(dǎo)讀》,陸九淵著,楊國(guó)榮導(dǎo)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3、《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牟宗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4、《新編中國(guó)哲學(xué)史·第三卷上冊(cè)》,勞思光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5、《中國(guó)哲學(xué)史新編·下冊(cè)》,馮友蘭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6、《中國(guó)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冊(cè)》,侯外廬主編,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
7、《中國(guó)思想史論集》,徐復(fù)觀著,上海書(shū)店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8、《中國(guó)近代思維的挫折》,(日)島田虔次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9、《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余英時(shí)著,三聯(lián)書(shū)店2004年第一版。
10、《宋明理學(xué)》,陳來(lái)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注釋:
[1]勞思光先生將理學(xué)發(fā)展分為三期:周、邵、張三子為初期的“天道觀”,二程、朱熹為中期的“本體論”,陸、王為后期的“心性論”。本文對(duì)宋儒的分類主要借鑒勞先生的看法。
[2]余英時(shí)先生深刻的指出:“以政治思維而論,宋代士大夫的‘創(chuàng)造少數(shù)'從一開(kāi)始便要求重建一個(gè)理想的人間秩序,當(dāng)時(shí)稱之為‘三代之治'。……由于對(duì)現(xiàn)狀的極端不滿,他們時(shí)時(shí)表現(xiàn)出徹底改造世界的沖動(dòng)。……用現(xiàn)代觀念說(shuō),他們已隱然以政治主體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遲疑的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這一主體意識(shí)普遍存在于宋代士大夫的創(chuàng)造少數(shù)之中,各種思想流派都莫能自外。從這個(gè)角度看,陸九淵的名言‘宇宙內(nèi)事,是己分內(nèi)事;己分內(nèi)事,是宇宙內(nèi)事'正是同一意識(shí)的一種表現(xiàn)。”
[3]楊國(guó)榮先生認(rèn)為:“陸九淵強(qiáng)調(diào)‘學(xué)茍知本,六經(jīng)皆我注腳',這種方法論原則無(wú)疑具有限制經(jīng)學(xué)獨(dú)斷論之意,但它同時(shí)亦容易導(dǎo)向師心自用。”這句話同時(shí)點(diǎn)出了心學(xué)可能的流弊。
[4]對(duì)于這點(diǎn),現(xiàn)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徐復(fù)觀先生都有討論。就本文最切近的,是余英時(shí)先生的話:“朱熹和許多理學(xué)家所熱烈追求的‘得君行道'的理想,為什么終于幻滅了呢?……大致說(shuō)來(lái),‘行道'之‘君'之難得其人和皇權(quán)的內(nèi)在限制同為不可忽視的兩大因素。”
[5]徐復(fù)觀先生認(rèn)為:“由伊川到朱子的這一條路,在實(shí)際上會(huì)發(fā)生兩個(gè)問(wèn)題:第一,因‘制外'太過(guò),容易使人的生命力受到束縛。一般說(shuō)道學(xué)家為拘迂,即系由此而來(lái)。第二,由此等細(xì)微末節(jié)下手,并不能真正保證一個(gè)人的大節(jié)無(wú)虧,并且有時(shí)還因枝節(jié)的拘牽,反忘記了本心的顯發(fā),甚或以此為作偽之資具。世人所罵的‘假道學(xué)',主要是從這些地方作假。”這段話最能洞見(jiàn)程朱學(xué)的弊病。
[6]這樣的一個(gè)歷史分期,是最近十幾年中國(guó)史學(xué)界一些學(xué)者在修正了日本學(xué)人(如內(nèi)藤湖南、島田虔次)的看法上形成的。日本學(xué)者認(rèn)為:“中國(guó)近代的成立,具有平民的發(fā)展與政治重要性的衰退這兩個(gè)根本特征”,“在思想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中,這兩個(gè)根本特征以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
[7]日本學(xué)者島田虔次在評(píng)價(jià)心學(xué)時(shí)曾指出:“(心學(xué))根本在于站在確信人的根本能動(dòng)性的立場(chǎng)上的不可遏止的自我擴(kuò)充的熱情以及與之互為表里的合理主義這兩種特殊的精神態(tài)度。”而這兩種精神,則恰恰是由象山最先也最鮮明的表現(xiàn)出來(lái)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