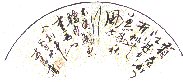內容提要:經濟社會的多極化發展也正是文化發展的現狀。文化的傳承發展決定著一批“與之相應的”文化人,而文化人的創造與延伸也在同時“創造著”文化,文化人的創造意識,責任意識,發展意識與文化的前途最終決定著社會的走向。文化研究必將涉及文化的發展態勢以及文化人的態度,考察我國當今的文化發展可以看出,“主流的、真正的、正常的”文化發展態勢并未形成,文化的前途尚堪憂慮,文化人的責任尚需“苛責”。本文將論證的基點放在文藝與社會上,探討了文化人的責任和文化的前途。
文化沒有確切的定義。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認為,“文化本身是為人類生命提供解釋系統,幫助他們對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1](P24)認為“就社會、團體和個人而言,文化是一種借助內聚力來維護本體身份[identity]的連續過程。這種內聚力的獲得則靠著前后如一美學觀念、有關自我的道德意識以及人們在裝飾家庭、打扮自己的客觀過程中所展示的生活方式和與其觀念相關的特殊趣味。文化因此而屬于感知范疇,屬于情感愈德操的范圍,屬于力圖整理這些情感的智識的領域。”[1](P82)文化的意義里面含有著個體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的強烈特征。然而文化的領域究竟還是意義的領域,筆者認為,文化的定義中應包含三層意義,即它是什么,它應怎樣以及衡量其發展的“標準”。
“文化人”則是個時髦的詞眼,以筆者觀點,他是從事文化發展創造和思想演進傳播的作家、學者、專家、大師一類人,且應當與“通俗化”的文化人即“知識分子”有所區別。特定時期的文化有“與之對應的”文化人,或落后而孜孜信守,或激進而疾呼駁辯,或沉穩而兼容并包,總之,俱是特定文化孕育的“產兒”。對于過去我們不能過于拘泥、沉迷;對于將來也未可盲目悲樂,但卻可以作合理性的“預見”。對于因循的傳統的挖掘總結和對于將來的可能性的預見,都正是為了現在著想,研究的真正的旨歸當在這個活脫脫離開而去,奔向未來的“現實存在”。
考察當今的文化和文化人概況,受著兩個大方面的影響。其一便是時間的影響;即過去和將來(包括現在)也即對傳統的審視和現實的認可;其二便是空間(地域)的影響,即國內外,說透了(在中國)就是東西方的差異。正是他們的論爭充斥著現實的文化空間,也決定著文化與文化人的明天。
一、我國當今文化及文化人的概況
文化的特征“決定著”文化人的特征,反過來文化人的創造也“決定著”文化的前程。轉型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化正面臨傳統與東西方的取舍。對東西方文化的取舍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對傳統的取舍。從清末到五.四運動再到建國后八十年代改革初期大規模大批量引進西方文化的浪潮,使中國文化人站到了取與舍的分界線上,是否告別“故去的迷夢”,面向現代的新生?一些人“振臂疾呼”,引進西方現代文明與自由的生活方式,無情批判傳統人文;一些人則慷慨陳詞,申言發揚“國統”,主張“西學為用,中學為體”。面對“自然選擇”,難免“首施兩端”。然而,科技的大發展,商業信息的流通,市場經濟的“實惠”卻似乎“有意無意”地助長了“向外”的勢頭,似乎正是大膽引進西方文化科技,摒棄中國的信守傳統,才使中國走向現代、走向發達的。國門的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孕育了這樣一批文化人,“私人化”正是他們的主要特征。“私人化”也即“只個人化”;“只個人化”雖也有“個性化”的成分,但最終不是真正的“個性化”。“個性化”是創作者最可寶貴的東西,或者說,創造本身即是“個性化過程”——不因循守舊,不迷信權威,不盲目模仿,而最注重現實的“多變”與靈魂的“自然延伸”。創造的個性是時代生活、民族文化精神與個人情感傾向、才能特征相互滲透熔合的產物。
西方文化的引進交融使一些飽受傳統文化“陰影折磨”的所謂“覺悟人”深切感受到西方文化空氣的自由、舒適,正是他們使只描寫“集團欲望”、“英雄主義”、“社會公德”的傳統心理意識走向“個人化”創作的進程,而熱衷于輔陳當今轉型時期和現代西方社會的以個人自然欲望的滿足為價值取向的生存“表象”。無可厚非,他們確實具有當前現實情境的信息量,也隱含著某些積極的發展勢頭,即具有“較深刻”的合理性,然而此種“合理性”卻與“符合理性”有所區別,且在現階段,也并不就是“符合理性”的。他們都以所謂“后現代主義”理論和“都市消費化”趨向日益明顯的“表象現實”為依據,而并沒有向深度探尋,沒有創造性、超越性精神框架的建構,意義背景狹窄單薄,文化價值虛渺匱乏。“引導資本主義文化的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原則”,造就了這樣一層人:“人們白天正派規矩,晚上卻放浪形骸,這就是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實質”。由人欲橫流到物欲橫流,“不僅突出體現了文化準則和社會結構準則的脫離,而且暴露出社會結構的自身極其嚴重的矛盾”。矛盾引發的危機,“給人們的動機造成了混亂,促成及時行樂意識,并破壞了從眾意識”,[1](P41)這些是西方人自己的表白,似乎更帶著客觀的意味,我們應該思考。現代的社會“物欲橫流”、“唯利是圖”,而“團結互助”的理念淡薄,致使精神文明的框架極難建構,不能不說是受了西方“自利主義”的“負作用”和本國某些文化人的膚淺宣揚的大影響。
“真實的”(即存在的)一定就“現實”嗎?我們探求的“現實”乃是“可持續發展”——長期的、積極向上有希望的、美麗溫馨的現實社會——不泯滅自我,同時注重團結、互助、美德與公利。而不是自私自利、唯我是尊的“人性疏離”的“冷酷”社會。
只個人化、個人性的“生存真實”不能等同于人類生存的真實;只講“個性”的“私人化”也不是生存的旨歸、自由的真諦!
二、我們的文化人的態度
(一)國內文化人的兩種態度——兩種“個人化”
“主持”文化的文化人不能不有一個“應有的,正確的”態度。我認為當前或者說已由來已久的存在著兩種“個人化”的發展態勢,對這兩種態勢的分析以及與西方文化人態度的參照對比無疑將有助于構建我們的文化人的精神品質。
1.個人化的“西化”——滿足表象
前面所說的自清末以來大批量引入西方自由文明所造成的許多弊端,可以說也正是由文化人的態度引發的。時代的變遷,時勢的推動,使一些淺薄從而不免盲目的文化人走進誤區:缺少民族文化的“自覺意識”,對傳統文化精神無端排斥。我們正期望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高智商”的文化人,發揚自家民族文化,還傳統文化的“真面目”,引進現代西方文明,以有助于國內建設,人民充實,意識更新,然而結果卻“不容樂觀”。有的倒真正地變成了民族文化的“叛逆”,成為西方狹隘自利文明的附庸:抨擊高雅、美德,張揚“下流”、“私欲”。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知識準備遠遜于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把握,遠遠沒有那些“學貫中西”的大家、學者們的博學宏富,也沒有現代西方文化的、他們筆下常引以為據的“開創者們”的“自覺精神”,要么對世俗生活做以淺見描述,要么對西方先哲智慧做以表層發揮,創作言論中時常見到海德格爾、馬克思、薩特、羅蘭、弗洛伊德、康德、巴托的影響,卻少見到獨創性的適合本國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創造;也常見到孔子、孟軻、老莊、朱熹和王陽明,但卻是始終自囿于前見的束縛,不做自己的考證研究,常用來做了比較戲謔和諷刺嘲罵的對象和口實。不言自明的后果的“啟因”正是文化人的態度和與之相關聯的所謂主流文化的“熏陶和孕育”。人為地、斷章取義地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意識、“個性化”創作相互對立起來,只埋頭于“復制”自由生活,翻譯“西言意境”,將創造性思維置于“硬性的模仿”和“惰性的束縛”之中,沒有遠見卓識的氣度,沒有廣納博收的胸懷,如此以往,中國的文化強勢何以才能體現?沒有“真正走進去”,又何以能“真正地走出來”?
2.個人化的“真空化”——純學術化
相對于上述的“個人化”,不知另一種文化人的態度是否也屬于“純個人化”的趨向?亞里士多德力倡“為學問而學問”,將知識分為兩種:一種是自由的哲理,它能使自由哲人通達真理的殿堂;二是實利的生產知能,那是卑下凡人的賤業。中國的董仲舒也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近代有些人主張作理想色彩的文化人,即保持思想的自由,使心志疏離于政治的風俗的時髦之外,視藝術為一目的而非手段,即王國維所謂“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而發達者”。此二種態度有重大的區別,但在深層次理解則都是“為學問而學問”,追求“學術的自由”。在我看來,前者有階級劃分的意識,人為地劃分等級、賢愚,無視平等;后者則難免疏離現實之虞。(錢鐘書說:“學問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江野老屋'中細細商量培養之事)但是,兩者都沒有研究范圍的限制,自然主張文化研究并無國界,應該互相引鑒吸收。
(二)西方文化人的態度——趨于“理性”
我只想說他們的“漢學研究”。談起中國文化人對待中國文化(文華)的態度時說要參照西方文化人,有時甚至都是悲哀的,而說要參照西方文化人的漢學研究則更其加重了悲哀的程度。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總序中說,“這套書可能會加深我們100年來懷有的危機感和失落感,它的學術水準也再次提醒:我們在現時代所面對的,決不再是過去那些粗蠻古樸、很快就將被中華文明所同化的、馬背上的戰勝者,而是高度發達的、必將對我們的根本價值取向大大觸動的文明”。[2](P1)利用別人的眼光來加深和提醒自知之明是英明的也是無奈的。說“無奈”是因為自知意識的“旁落”,說“英明”則不僅是指這是對待“無奈”的態度,也同時可為我們的真正文化人在進行文化交流和意識傳輸過程中提供一個“端口”——超越“自主的局限”去思量自身并進而“知其所想”。如果說伏爾泰、孟德斯鳩、魁奈、黑格爾的“中國觀點”還帶有世紀前的片面和自私的話,那末從李約瑟、費正清、白壁德、杜維明、麥克馬倫到日本“漢蟲”的“漢學研究”則充分閃爍著理性的光澤。在此,不敢羅列其著作了,因為其遍及方方面面和意識內外(包括形而上的)的精微獨到只會讓我們的有識之士汗顏和驚悚;而且,他們自己的本土化著作也常常是所謂“西化人士”們遠征近引的“經典”。可見,他們的漢學研究是在其“本土意識”的指導和引領下進行的,是其漢學的“本土化結晶”。對于文化(引進、研究),這當是理性的、誠懇的和真實不欺的行為態度。
另一方面還要注意到,西方文化人的漢學研究沒有成為我們的文化人文化研究態度的參照取向,反而成為膚淺“護道”之士津津樂道的、無端盲目自我夸耀的所謂“力證”,則又是我國文化人的悲哀。
(三)文化人的“責任化”——我們的文化人應有的態度
既然文化人的創造、取舍和態度影響著文化的發展,那么面對當今的文化人和文化的現狀,真正的文化人“應有”怎樣的態度呢?拙見以為當具下述的幾點。
1.正是科學的研究精神
何謂“科學的”呢?即須具有實證考據的態度;具有剖辯、發揚的氣度;具有不斷章取義的廣度。現代的法制社會不是最注重證據嗎,文化的研究也正需要有此種實證的精神。“細細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細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參考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地義的信條”。[3]“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來[4],這些正是實證的功用,沒有實證,便沒有論辯、發揚的氣度,便沒有客觀真實的論見。例如,傳統的“利”、“欲”說,就不能只認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便斷定孔子反對所有的“利”,為何不看看《論語》上的另一段話呢?《論語》上說,“子適衛冉有仆。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5](P85)可見他并不反對所有的“利”,而是反對個人自營的私利。有了這樣的實證,便不致認為孔子將“義、利”決然對立,非此即彼。又如對“欲”說,人們也普遍認為儒家向來主張“絕欲”,卻如何無視“去人欲”乃是后來宋儒理學的“發展”,考察了先儒孔子關于“禮”的解說也便不致認定孔子主張“絕欲”了。美國的丹尼爾·貝爾也認為,“文化本身是為人類生命提供解釋系統,幫助他們對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所以,傳統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記憶連貫,告訴人們先人們是如何處理同樣的生存困境的”。[1](P24)文化的傳統豈能無端摒棄。
2.是責任意識與“說教”功能
文化人的創作與思想建樹倘若沒有指導現實、凈化社會,發揚真、善、美的功用與憂患意識,便也失去了存在的真價值。秘魯結構主義大師略薩說:“文學是對社會的發言”;馬爾庫賽說:“人的解放的根本標志和現實途徑,便是以藝術——文化為手段對心理——本能壓抑的消除”(見其著《論解放》)。丹尼爾·貝爾認為,“社會上的個人主義精神氣質,其好的一面是要維護個人自由的觀念,其壞的一面則是要逃避群體社會規定的個人應負的社會責任和個人為社會應作出的犧牲”。[1](P308)現在也有學者指出,文學應是強者,允許發泄者的恣睢就是對文明的自戕;文化也應該是對于平庸的超越。社會存在和人為欲求需要文化的發揚傳播以及創造承擔一定的“說教”功能,以用來指導被庸俗私欲和外來誤導侵蝕而漸迷茫、墮落和消沉的人們,而這其實也是文化發展本身的責任。
3.應有兼容并蓄的胸襟
面對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的當今社會,而“文化的根本在經濟”,文化的“一體化”也就必然應有積極交流,兼容并蓄的心胸。但面對于此,卻不得不有“兩個超越”,不得不有如此的態度:“不取鄉愿的,紊亂是非的,助長懶性的,阻礙進化的,沒有自己立腳地的調和論調;不取虛無的,不著邊際的,沒有信仰的,沒有主張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6]對待兩種文化應先有“平等對待”的氣度,做到“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引進、研究的目的俱在“革新”并從而為我所用,魯迅所謂“不能革新的人種,怕也不能保古的”,[7](P43)“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內之仍費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8](P44)不正是引用傳統,引用西方的目的嗎? 然而,此種取舍,也似乎應有個“時間的先后問題”,既不能在完全空白、無知的基礎上進行。中國人則應當在起碼理解中國人文環境的基礎上再來談引用西方,再來談批判傳統。“面對神秘之際,我們的敬畏之感,往往使我們不能領受到:把剖析與深入視同一體時所能獲致的滿足”,[9](P1)不要被傳統的或西方的任何一種“神秘”而使自己“神魂顛倒了”,目迷五色了。西方文化人研究漢學的態度和路徑對我們起碼應是個警醒。
三、結語
對于當今文化的現狀,文化人不得不應有以上三個“約束”,缺一不可。研究的責任、創造的責任,兼容的責任,句句在責任的訴求之中,此種責任不是人為強加的,而應當是追求真善美的積極文化人的“自然行為”與“自覺精神”,舍此,此文化前途或真可堪憂了。
最后還要拿魯迅的一段話來作本文的結尾。魯迅說:“夫國民發展,功雖在于懷古,然其懷也,思想朗然,如鑒明鏡,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悅,則長夜之始,即在斯時”,[10](P65)或可作為當今文化人的借鑒和應有。
參考文獻:
[1]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89(41、24頁);
[2][美]包壁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3]胡適·我的歧路·胡適文存二之三[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4]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胡適文存三之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5]胡適·孔子·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P84-86);
[6]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卷[C],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84(428頁);
[7]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43頁);
[8]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44頁);
[9]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序·陳曉林譯[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
[10]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65頁);
另參考散見于《文化研究》[J],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6-1997(1-12期)有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