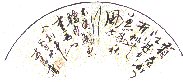內(nèi)容提要:本文主要分為四個(gè)大的部分,第一部分簡(jiǎn)要介紹了徐中舒先生的生平事跡和國(guó)內(nèi)著名學(xué)者對(duì)他的評(píng)價(jià),是對(duì)于徐先生一個(gè)概括性的整體把握;第二部分闡述和分析了徐中舒先生學(xué)術(shù)思想的“源”,著重強(qiáng)調(diào)了桐城學(xué)派、王國(guó)維、梁?jiǎn)⒊⒗顫?jì)、傅斯年等人對(duì)于徐先生學(xué)術(shù)思想的形成和確立的重要影響;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徐先生學(xué)術(shù)思想的主要特點(diǎn)——“預(yù)流”和對(duì)于“二重證據(jù)法”的發(fā)展;最后一部分作為總結(jié),同時(shí)兼緬懷徐先生。
關(guān)鍵詞:王國(guó)維;梁?jiǎn)⒊皇氛Z(yǔ)所;動(dòng)靜相宜;預(yù)流;二重證據(jù)法
一、徐中舒先生生平事跡及國(guó)內(nèi)著名學(xué)者對(duì)之的評(píng)價(jià)
徐中舒(1898-1991)先生是中國(guó)歷史學(xué)家、古文字學(xué)家。初名道威。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1925年考入國(guó)立清華大學(xué)國(guó)學(xué)研究院。1928年任復(fù)旦大學(xué)和暨南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詩(shī)十九首考》一文受陳寅恪賞識(shí),1930年經(jīng)其推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兩年后升為研究員。在歷史語(yǔ)言研究所九年,發(fā)表一系列學(xué)術(shù)論著,受到學(xué)術(shù)界的重視。30年代初期參加整理清代內(nèi)閣大庫(kù)所藏明清檔案,頗著成績(jī);同時(shí)在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兼課,講授“殷周史料”。1934年與容庚等共同發(fā)起成立考古學(xué)社。1937年抗日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應(yīng)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xué)協(xié)聘,任四川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從40年代起,他先后還在樂(lè)山武漢大學(xué)、成都燕京大學(xué)、華西協(xié)和大學(xué)、南京中央大學(xué)執(zhí)教。1949年以后除繼續(xù)擔(dān)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省博物館館長(zhǎng)、中國(guó)科學(xué)院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學(xué)部委員、國(guó)務(wù)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wèn)、四川省歷史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中國(guó)先秦史學(xué)會(huì)理事長(zhǎng)、中國(guó)古文字學(xué)會(huì)常務(wù)理事、中國(guó)考古學(xué)會(huì)名譽(yù)理事,以及《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shū)·中國(guó)歷史》編輯委員會(huì)委員等職務(wù)。
徐先生一生可謂成果卓著、著作等身。應(yīng)該說(shuō),按照錢穆先生的標(biāo)準(zhǔn),徐先生不能算作一位通才,但是優(yōu)秀史學(xué)家的標(biāo)準(zhǔn)不止一種,在先秦史、古文字學(xué)、古器物學(xué)、考古學(xué)等方面徐先生確實(shí)一位了不得的人物。我們這里姑且引用王曉清先生在《學(xué)者的師承與家派》中關(guān)于徐中舒學(xué)記的結(jié)語(yǔ)做一評(píng)述:“王國(guó)維是新史學(xué)的開(kāi)山祖,作為王國(guó)維親炙弟子,徐中舒在中國(guó)歷史學(xué)領(lǐng)域的地位是顯而易見(jiàn)的。成就學(xué)術(shù)聲名的徐中舒在民國(guó)時(shí)期成果疊出,在共和國(guó)時(shí)期也是碩果累累。1980年,中國(guó)史學(xué)會(huì)在北京重建,82歲的徐中舒以很高的得票當(dāng)選為中國(guó)史學(xué)會(huì)理事。在97歲的人生旅程里,徐中舒的《先秦史論稿》、《論巴蜀文化》、《甲骨文字典》等著作為中國(guó)歷史學(xué)的科學(xué)體系化刻寫了不朽的碑銘。”(1)四川大學(xué)著名古文字專家、徐中舒先生晚年的學(xué)生彭裕商教授曾經(jīng)這樣評(píng)價(jià)徐先生的學(xué)術(shù)成就和人師風(fēng)范:“王、梁等人為學(xué)界巨子,學(xué)貫古今,涉獵甚廣。先生承其學(xué)風(fēng),學(xué)路寬廣,在先秦史、古文字學(xué)、考古學(xué)、地方史、民族學(xué)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撰寫論文100多篇,專著數(shù)冊(cè),多有獨(dú)到之處。”(2)“(徐)先生作為一代學(xué)術(shù)大師,不僅于學(xué)術(shù)有重大貢獻(xiàn),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強(qiáng)烈的愛(ài)國(guó)熱情,自強(qiáng)不息,誨人不倦,提攜后學(xué),誠(chéng)以待人。”(3)此外這里還要著重指出的是,徐先生不但精于致學(xué),亦善于任事。“至1937年抗日軍興,八月,中研院開(kāi)始南遷,十月,徐先生負(fù)責(zé)押運(yùn)已整理就緒的明清檔案等物資由南京沿長(zhǎng)江經(jīng)洞庭湖至長(zhǎng)沙的任務(wù)。無(wú)怪乎傅所長(zhǎng)在致蔡元培院長(zhǎng)的一信中高度評(píng)價(jià)徐先生這一方面的工作:‘檔案整理,已可作第二步刊行。中舒先生善于布置,有事務(wù)長(zhǎng)才,故工作進(jìn)行得以迅速,至可喜也。'”(4)由此可見(jiàn),徐中舒先生無(wú)論是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上,還是在為人治事上都可謂是“人中之杰”。
二、徐中舒先生學(xué)術(shù)思想的“源”
1.徐中舒先生早年受到桐城學(xué)派的影響
徐中舒先生是安徽安慶人,1914年進(jìn)入安慶初級(jí)師范學(xué)校學(xué)習(xí),在師范學(xué)習(xí)的三年時(shí)間里,“徐先生受國(guó)文老師胡遠(yuǎn)浚先生的影響最大”(5)胡遠(yuǎn)浚先生擅長(zhǎng)桐城派古文,與桐城派的最后一位巨子吳汝綸(字贄甫)有交情。(6)徐先生作為他的學(xué)生,也就不免受到其深刻的影響。桐城學(xué)派要義理、詞章、考據(jù)三者并重,徐先生便要求自己從這三方面充實(shí)自己。關(guān)于桐城派對(duì)于徐中舒先生啟蒙式的影響,我們可以從徐中舒先生于1987年第六期《文史知識(shí)》上發(fā)表的文章《我的學(xué)習(xí)之路》中窺見(jiàn)一二:“桐城古文派以復(fù)古為革新,復(fù)古即‘非三代兩漢之書(shū)不敢視',革新則主張‘惟陳言之務(wù)去',一掃明清以來(lái)的四六駢體文和八股的陳詞濫調(diào),提倡做明白淺顯的古文,……師范的三年學(xué)習(xí),我將絕大部分時(shí)間和精力都集注于國(guó)文課,其余功課只求及格就行了。學(xué)有偏愛(ài),這為我以后的學(xué)業(yè)規(guī)定了方向和范圍。”(7)誠(chéng)然,縱觀徐先生一生的研究方向和學(xué)術(shù)思想來(lái)看,雖然與桐城學(xué)派有著很大的區(qū)別。但是,我們應(yīng)該看到,先生之所以后來(lái)又如此豐碩的成果,與其當(dāng)時(shí)在師范就讀三年所受的國(guó)學(xué)熏陶,尤其是桐城學(xué)派治學(xué)思想的影響是不無(wú)關(guān)系的。應(yīng)該說(shuō)正是這一時(shí)期的學(xué)習(xí),初步奠定了其國(guó)學(xué)的基礎(chǔ)。成為了徐先生一生學(xué)術(shù)事業(yè)的開(kāi)端。
2.王國(guó)維先生對(duì)于徐先生的影響
徐中舒先生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xué)國(guó)學(xué)研究院后,師從王國(guó)維、梁?jiǎn)⒊②w元任、李濟(jì)諸先生。而這其中對(duì)于徐先生影響最大恐怕還當(dāng)數(shù)王靜安先生。這不僅是因?yàn)樾煜壬趪?guó)學(xué)研究院期間主要師從王國(guó)維,更是由于在學(xué)術(shù)興趣和學(xué)術(shù)思想上二人可謂是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尤其是王國(guó)維的“古史二重證據(jù)法”對(duì)于他形成獨(dú)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風(fēng)格有著甚為重大的關(guān)系。王在《古史新證》的總結(jié)中講:“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以據(jù)以補(bǔ)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shū)之某部分全為實(shí)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wú)表示一面之事實(shí)。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shū)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8)王對(duì)二重證據(jù)法的運(yùn)用,成功地開(kāi)辟了研究商周史的新途徑,在客觀上對(duì)其后建立在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研究方法與歷史唯物主義基礎(chǔ)之上的先秦史學(xué)的形成具有促進(jìn)作用。后來(lái)徐中舒先生從事先秦史和西南民族史方面研究是就十分注重利用考古學(xué)、民族學(xué)、民俗學(xué)、人類學(xué)等其他方面的知識(shí),這種多學(xué)科交叉研究、相互印證的方法是徐先生后來(lái)治學(xué)的一大特點(diǎn),從這一層上來(lái)說(shuō),王國(guó)維先生的學(xué)術(shù)思想尤其是其在古史研究上的“二重證據(jù)法”理論對(duì)于徐中舒先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yuǎn)的。
3.梁?jiǎn)⒊⒗顫?jì)對(duì)于徐中舒先生的影響
“過(guò)去的研究一般認(rèn)為在國(guó)學(xué)院的學(xué)習(xí)期間,徐先生受王國(guó)維影響甚巨。其實(shí),在這一年的學(xué)習(xí)中,徐先生同時(shí)受到了多方面的影響。”(9)例如徐中舒先生在研究員畢業(yè)時(shí)提交的兩篇論文,就是由梁?jiǎn)⒊壬屯鯂?guó)維先生分別指導(dǎo)的。據(jù)周書(shū)燦先生的分析“徐中舒在清華研究院讀研究生期間,梁?jiǎn)⒊v授中國(guó)歷史研究法,徐對(duì)梁?jiǎn)⒊恼n頗感興趣。耳聞目睹再加上自己親身的學(xué)術(shù)實(shí)踐,徐在古史研究中形成了獨(dú)到而完善的治學(xué)門徑,尤其對(duì)文獻(xiàn)具有精深的造詣,重視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鑒別辨析,得心應(yīng)手地駕馭和利用,可以說(shuō)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梁?jiǎn)⒊难詡魃斫逃忻芮新?lián)系。”(10)梁?jiǎn)⒊鳛橹袊?guó)近代新史學(xué)的開(kāi)山之祖,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上可謂是頗多創(chuàng)見(jiàn),尤其是其廣歷史研究法的理論,如果認(rèn)為其不對(duì)于正在清華國(guó)學(xué)研究院求學(xué)的徐中舒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恐怕是說(shuō)不過(guò)去的。
應(yīng)該說(shuō)梁?jiǎn)⒊壬鷮?duì)于徐中舒先生的影響主要是在治史的指導(dǎo)思想和研究方法領(lǐng)域,而從國(guó)外留學(xué)歸來(lái)的中國(guó)第一位接受過(guò)專業(yè)的近代考古學(xué)訓(xùn)練的學(xué)者——李濟(jì)對(duì)于徐先生的影響就更多了體現(xiàn)在了知識(shí)和研究領(lǐng)域的擴(kuò)展這一點(diǎn)上。“盡管在這一年里,李濟(jì)先生因忙于西陰村的考古調(diào)查,在研究院的時(shí)間很少,指導(dǎo)范圍為‘中國(guó)人種考',開(kāi)課亦僅限于‘民族學(xué)',但對(duì)于受桐城文派‘惟陳言之務(wù)去'影響至深、且又接受了西方進(jìn)化論思想的徐先生來(lái)說(shuō),李濟(jì)先生講授的近代考古學(xué)和人類學(xué)這樣一些嶄新的知識(shí)有著無(wú)比巨大的吸引力。”(11)徐先生后來(lái)之所以能夠得心應(yīng)手的利用考古學(xué)、人類學(xué)、民族學(xué)等其他學(xué)科的知識(shí)來(lái)為自己的研究服務(wù),與這一時(shí)期在李濟(jì)先生那里受到的專業(yè)訓(xùn)練是分不開(kāi)的,這也成為他與那一時(shí)期國(guó)內(nèi)其他學(xué)者相比的一點(diǎn)優(yōu)勢(shì)所在。
4.在史語(yǔ)所工作的九年對(duì)于徐中舒先生學(xué)書(shū)思想的影響
應(yīng)該說(shuō)徐先生在史語(yǔ)所的九年時(shí)間是史語(yǔ)所歷史上最為輝煌和成就最為卓著的時(shí)期之一。這一時(shí)期的史語(yǔ)所已經(jīng)從最初“從無(wú)到有”的初創(chuàng)階段進(jìn)入了一個(gè)相對(duì)成熟和穩(wěn)定的發(fā)展時(shí)期。就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內(nèi)國(guó)際環(huán)境來(lái)看,20世紀(jì)20年代雖然是一個(gè)軍閥混戰(zhàn)的時(shí)期,但是正是因?yàn)檫@一點(diǎn),當(dāng)時(shí)的統(tǒng)治者對(duì)于思想界和學(xué)界的控制就有一些力不能及,這也為這一時(shí)期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gè)相對(duì)自由的空氣。同時(shí),“史語(yǔ)所在傅所長(zhǎng)的經(jīng)營(yíng)下,無(wú)論是在資料的搜集方面,還是研究經(jīng)費(fèi)的充足,都具備了國(guó)內(nèi)最優(yōu)越的研究條件,更重要的是各種人才濟(jì)濟(jì)一堂以進(jìn)行‘集中的工作',傅斯年、陳寅恪、李濟(jì)、趙元任、董作賓諸先生皆學(xué)有專長(zhǎng)并視野開(kāi)闊、眼光獨(dú)到。”(12)正是由于當(dāng)時(shí)的歷史語(yǔ)言研究所具備了非常良好的內(nèi)部和外部環(huán)境,使得這里成為了一塊歷史學(xué)研究的圣地。徐先生在這里也是如魚(yú)得水。正是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學(xué)術(shù)氛圍和徐中舒先生自身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他在古代史研究方面發(fā)表論文著述近三十篇(種),迎來(lái)了自己在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第一個(gè)輝煌時(shí)期。
這里我認(rèn)為還有必要提一提當(dāng)時(shí)史語(yǔ)所的所長(zhǎng)傅斯年先生對(duì)于徐先生的影響。傅斯年先生認(rèn)為“近代的歷史學(xué)只是史料學(xué)”(13)而我們從徐中舒先生在這一時(shí)期發(fā)表的學(xué)術(shù)論著中體現(xiàn)的研究方法來(lái)看,真可謂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dòng)手動(dòng)腳找東西”,徐先生自己也說(shuō)“史家不能無(wú)史料而為史”。(14)雖然不似傅斯年的話那么絕對(duì),但是以史料作為治史的根本這一思想是顯而易見(jiàn)的。
三、徐中舒先生學(xué)術(shù)思想的“流”
1.徐中舒學(xué)術(shù)思想中的“動(dòng)靜相宜”——“預(yù)流”
陳寅恪先生有一句名言:“一時(shí)代之學(xué)術(shù),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wèn)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wèn)題,則為此時(shí)代學(xué)術(shù)之新潮流。治學(xué)之士,得預(yù)于此潮流者,謂之預(yù)流。其未得預(yù)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xué)術(shù)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5)所謂“預(yù)流”就是始終處在歷史學(xué)發(fā)展的漩流的中心。我們這里且引用王曉清先生的評(píng)述做一說(shuō)明:“徐中舒沒(méi)有一意奔兢于學(xué)術(shù)風(fēng)潮,也沒(méi)有刻意追趕學(xué)術(shù)浪頭,而是以自己所信守的研究方式方法在為歷史學(xué)提供堅(jiān)實(shí)而可以引據(jù)的學(xué)術(shù)結(jié)論。”(16)在20世紀(jì)紛繁復(fù)雜的歷史變遷中,中國(guó)的史學(xué)風(fēng)潮一個(gè)接著一個(gè),從古史辨派到釋古,從實(shí)證主義到歷史唯物主義,數(shù)十年間,中國(guó)的史學(xué)研究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徐中舒先生無(wú)論是從研究的領(lǐng)域還是從研究的基本方法上來(lái)說(shuō)都保持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他的觀點(diǎn)無(wú)論是在20年、30年代、50年代還是在今天,仍然沒(méi)有為時(shí)代所湮沒(méi)。這是為什么呢?應(yīng)該說(shuō)這是徐先生一生致力于扎實(shí)治學(xué),始終堅(jiān)守學(xué)人的學(xué)術(shù)原則和操守的結(jié)果。即便是在60年代左傾錯(cuò)誤嚴(yán)重和后來(lái)的文化大革命時(shí)期,徐先生受盡迫害和非難,也是始終堅(jiān)定如一。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預(yù)流”,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有著自身的軌跡,我們不應(yīng)該死抱住自己的理論而不能夠推陳出新,跟上時(shí)代發(fā)展的潮流和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大勢(shì)。但是在具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lǐng)域上,如果我們不能夠有所取舍專攻,而是一味的隨波逐流的話,我們很可能最終一事無(wú)成。徐中舒先生的成功就在于他把跟上學(xué)術(shù)潮流的發(fā)展大勢(shì)與堅(jiān)守自己的研究領(lǐng)域和研究方法統(tǒng)一起來(lái)。如果我們把前者看作“動(dòng)”,后者看作“靜”,那么徐先生真可謂做到了動(dòng)靜相宜。正是因?yàn)樾熘惺嫦壬擅畹奶幚砹诉@一動(dòng)與靜的關(guān)系,他才能始終站立在學(xué)術(shù)漩流的中心地帶,在數(shù)十年的時(shí)間里始終代表了先秦史研究領(lǐng)域的中堅(jiān)力量。
2.從二重證據(jù)到多重證據(jù)——徐中舒對(duì)于王國(guó)維“二重證據(jù)法”的發(fā)展
前面已經(jīng)提到過(guò),徐中舒先生深受王國(guó)維先生二重證據(jù)法的影響。應(yīng)該說(shuō)他在這以后的研究中接受并發(fā)展了這一重要的治史方法。下面我們分?jǐn)?shù)個(gè)方面做一簡(jiǎn)要說(shuō)明
1)對(duì)出土古文字研究的發(fā)展:用地下出土的甲骨金文考證古代的歷史,是王國(guó)維先生首先開(kāi)創(chuàng)的,徐中舒對(duì)此深有體會(huì)并將之應(yīng)用于自己的研究當(dāng)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僅以古文字記錄的古代史事為史料,而且更發(fā)現(xiàn)古文字本身即為最好的古代史料”(17)這一點(diǎn)在他的《耒耜考》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由于傳世文獻(xiàn)記載的不足,徐先生大量使用了甲骨文、古代錢幣、漢畫(huà)像石和日本鋤等資料,取‘古文字中由耒耜孳乳之字'與其他資料互相參證,這無(wú)疑是將‘古史二重證據(jù)法'向前推進(jìn)了一大步。”(18)
2)對(duì)于考古學(xué)資料的重視:王國(guó)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中所謂“地下之新材料”基本上是局限在古代文字者一方面,而近代考古學(xué)是十分強(qiáng)調(diào)的古代遺址、遺跡、遺物的,王先生因無(wú)法見(jiàn)到未曾涉及。隨著20-30年代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安陽(yáng)殷墟遺址發(fā)掘工作的蓬勃開(kāi)展,考古材料對(duì)于闡釋中國(guó)古史中的疑難問(wèn)題的重要性就逐步體現(xiàn)出來(lái)了。羅志田在《史料的盡量擴(kuò)充與不讀二十四史》中談到:“過(guò)去的學(xué)術(shù)史研究特別注重王國(guó)維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其實(shí)當(dāng)時(shí)僅任清華大學(xué)研究院講師的李濟(jì)恐怕對(duì)實(shí)際研究的影響還更大,特別是在地下證據(jù)由文字向?qū)嵨镛D(zhuǎn)換這方面,李氏的劃時(shí)代影響無(wú)人能及。從徐中舒登人治學(xué)的變化可以看出,從王國(guó)維道李濟(jì)這一路向的發(fā)展后來(lái)基本落實(shí)在史語(yǔ)所”(19)“盡管徐先生一生中從未參加過(guò)田野考古發(fā)掘,但他卻深知科學(xué)發(fā)掘的重大意義”(20)這一點(diǎn)從他對(duì)于古代金石學(xué)予以的嚴(yán)厲批評(píng)中可以看出。此外還有一點(diǎn)可以證明徐先生對(duì)于科學(xué)的考古工作的重視:“與徐中舒同年的著名考古學(xué)家馮漢驥,雖與徐中舒的學(xué)術(shù)道路不盡一致,但兩人相交四十多年,論學(xué)為人一致,關(guān)系甚為密切。”(21)綜合以上數(shù)例,可以看出徐中舒對(duì)于考古學(xué)的重要意義的認(rèn)識(shí)已經(jīng)發(fā)展和延伸了王國(guó)維的理論,他成為了較早利用考古學(xué)材料(不僅限于文字材料)研究中國(guó)古代歷史尤其是上古歷史的著名學(xué)者之一。
3)對(duì)古器物中包含的古代歷史信息的發(fā)掘:1947年11月,徐先生被提名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在“合于院士候選人資格之根據(jù)”一欄,徐先生作為候選人資格的理由是“用古文字與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22)。通過(guò)古器物來(lái)研究古代文化、生產(chǎn)、生活狀況,這在徐先生一生的研究中,占有較大的比重。進(jìn)入史語(yǔ)所及其后數(shù)十年間,徐先生在古器物的研究領(lǐng)域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論文。《耒耜考》、《古代狩獵圖像考》、《說(shuō)尊彝》、《蜀錦》、《談古玉》、《論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貢獻(xiàn)——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lái)》等都是其代表作品。這里我們應(yīng)該著重看到一點(diǎn),與中國(guó)古代的歐陽(yáng)修、趙明誠(chéng)等金石學(xué)家以及古董玩家們不同的是,徐中舒先生所關(guān)注的主要不是古物本身所具有的價(jià)值或者其精美程度等,而是集中關(guān)注古物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從而將之從沉淀數(shù)千年的古物中抽取出來(lái),為歷史研究服務(wù)。因此,我們說(shuō)徐中舒先生對(duì)于古器物的研究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xué)性的研究,是對(duì)于王國(guó)維先生二重證據(jù)法的重要補(bǔ)充和發(fā)展。
4)將民族學(xué)與古史研究相結(jié)合:隨著近代以來(lái)民族學(xué)、人類學(xué)的發(fā)展,今天的歷史研究中將這些學(xué)科與歷史學(xué)科進(jìn)行交叉研究已經(jīng)是一件司空見(jiàn)慣的事情,但是在當(dāng)時(shí)這實(shí)在可以稱得上是一個(gè)了不起的創(chuàng)新。陳寅恪先生在總結(jié)王國(guó)維先生“學(xué)術(shù)內(nèi)容及治學(xué)方法”時(shí),曾提到“取異族之故書(shū)與吾國(guó)之舊籍互相補(bǔ)正”之法。這一點(diǎn)似乎并非王靜安所創(chuàng),乃是陳先生夫子自道也。徐中舒先生深得這一要旨,雖然因?yàn)楫?dāng)時(shí)的條件限制,不能取異族之書(shū)補(bǔ)正中國(guó)舊籍,但是他在研究中國(guó)古代史時(shí)大量使用中國(guó)傳世文獻(xiàn)與大量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民族調(diào)查資料相互參照進(jìn)行研究。徐先生認(rèn)為:“凡是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相同的民族,生產(chǎn)關(guān)系發(fā)展到一定的時(shí)候,都應(yīng)當(dāng)有相同的、一定的形式。”“所謂不雅訓(xùn)的神怪之言,我們通過(guò)對(duì)民族學(xué)的研究,從這些神怪之言中找出古代的一些基本史實(shí),就是素地”(23)。這一點(diǎn)現(xiàn)在看來(lái)雖然未見(jiàn)的十分正確,但是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人們打破夷夏之防,充分利用民族學(xué)資料開(kāi)拓史學(xué)研究的新視界應(yīng)該說(shuō)是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的。直到近年,羅志田教授的《〈山海經(jīng)〉與中國(guó)近代史學(xué)》仍然談到了對(duì)于像《山海經(jīng)》這樣的“神怪之言”中包含的歷史信息的解讀這一問(wèn)題,由此可見(jiàn)這一思想對(duì)于我們研究上古歷史有著多么重大的意義和何等深遠(yuǎn)的影響。
四、結(jié)論
由此我們便對(duì)于徐中舒先生的學(xué)術(shù)思想的“源”與“流”有一個(gè)初淺的了解。我們研究徐中舒先生的學(xué)術(shù)思想不能只看徐先生的研究論著,而是應(yīng)該把徐先生的學(xué)術(shù)思想放在20世紀(jì)前半期中國(guó)史學(xué)發(fā)展和流變的大背景、大環(huán)境下來(lái)進(jìn)行研究。如果我們不能看到這一點(diǎn),那就是以管窺天而不能知其全貌,所謂“神龍見(jiàn)首不見(jiàn)尾”。如果沒(méi)有王國(guó)維先生“二重證據(jù)法”的提出,如果沒(méi)有梁?jiǎn)⒊方绺锩奶?hào)角,如果沒(méi)有李濟(jì)先生把近代考古學(xué)和人類學(xué)的知識(shí)帶到中國(guó),如果沒(méi)有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及其“疑古”思潮,如果沒(méi)有傅斯年歷史語(yǔ)言研究所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徐先生的學(xué)術(shù)軌跡和學(xué)識(shí)思想也許完全不是現(xiàn)在的這個(gè)樣子,這也就是我寫這篇小文的目的,即是通過(guò)徐中舒先生一人為一個(gè)切入點(diǎn),來(lái)試圖窺探整個(gè)20世紀(jì)上半葉中國(guó)史學(xué)界的發(fā)展軌跡和流變過(guò)程。
徐中舒先生一生為師,可謂“桃李滿天下”,其中較為有名的有童恩正、彭裕商等諸先生,后來(lái)都成為了先秦史和古文字研究領(lǐng)域的翹楚。作為一位學(xué)者,他可謂著作等身、成就斐然;而作為四川大學(xué)歷史系最有名望的教授之一,他也是兢兢業(yè)業(yè)、盡職盡責(zé),直到晚年仍然教學(xué)不輟。應(yīng)該說(shuō)徐先生不僅是學(xué)術(shù)界的精英,也是川大名師,為川大的發(fā)展尤其是歷史學(xué)科的發(fā)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xiàn)。最后我用彭裕商先生的話作結(ji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給了后人不朽的學(xué)術(shù)成果和高尚的人師風(fēng)范,為后人所景仰。作為一代學(xué)術(shù)大師,先生德業(yè)長(zhǎng)存。”(24)
注釋:
(1)王曉清,《學(xué)者的師承與家派》,湖北長(zhǎng)江出版集團(tuán)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12頁(yè)
(2)彭裕商,《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jì)念》,《歷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3)彭裕商,《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jì)念》,《歷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4)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3頁(yè)
(5)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頁(yè)
(6)參見(jiàn)《安慶市志》第1842頁(yè),待刊,轉(zhuǎn)引自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頁(yè)
(7)徐中舒,《我的學(xué)習(xí)之路》,《文史知識(shí)》,1987年第六期
(8)朱鳳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9)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5-6頁(yè)
(10)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史論壇于2003-10-1723:59:37發(fā)布(網(wǎng)上資料)
(11)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6頁(yè)
(12)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3頁(yè)
(13)傅斯年著《歷史語(yǔ)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中國(gu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傅斯年卷》,第349頁(yè)
(14)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載《史語(yǔ)所集刊》七分一本,1936。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集》,第652-691頁(yè)
(15)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史語(yǔ)所集刊》一本二分。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lián)書(shū)店,2001,第266-268頁(yè)
(16)王曉清,《學(xué)者的師承與家派》,湖北長(zhǎng)江出版集團(tuán)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08頁(yè)
(17)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5頁(yè)
(18)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5頁(yè)
(19)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kuò)充與不讀二十四史》,《歷史研究》,2000年第四期
(20)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3頁(yè)
(21)王曉清,《學(xué)者的師承與家派》,湖北長(zhǎng)江出版集團(tuán)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11頁(yè)
(22)《中央研究院史初考》第205頁(yè),1988年6月,轉(zhuǎn)引自徐中舒著、徐亮工整理,《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4頁(yè)
(23)徐中舒,《1982年先秦史專題講課記錄》(未刊),第39頁(yè)、34頁(yè)
(24)彭裕商,《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jì)念》,《歷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第六部分:主要參考書(shū)目
王曉清,《學(xué)者的師承與家派》,湖北長(zhǎng)江出版集團(tuán)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xué)·徐中舒卷》,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6
朱鳳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歷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歷史研究》,2000年第四期
《文史知識(shí)》,1987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