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詮釋學從一門解釋的技術逐漸發展為一種方法論和本體論,在西方哲學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現代詮釋學在本質上是本體論,但其方法論的價值無法忽略。語言作為詮釋學的核心,其作用在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認識自我的過程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語言轉向”在西方史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回應。后現代史學的哲學基礎最早可追溯至此。歷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的研究,應當合理地吸收哲學詮釋學以及后現代史學的某些觀點,以期在“真實”與“現實”之間達致平衡。
關鍵詞:詮釋學;語言轉向;后現代史學;思想史
一、作為方法論的詮釋學和作為本體論的哲學詮釋學
詮釋學( Hermeneutik )作為宣告、口譯、闡明和解釋的技術,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存在。赫爾墨斯 (Hermes) 是上帝一位信使的名字,他給人們傳遞上帝的消息,解釋上帝的指令,并將上帝的指令翻譯成人間的語言,使凡人可以理解,因此詮釋學引申而成為一種關于理解和解釋的技藝學。
“詮釋學”作為書名第一次出現是在 1654 年,作者為 J.Dannhauer 。后來詮釋學沿兩條路線發展下去:神學的詮釋學和語文學的詮釋學。神學詮釋學是一種正確解釋《圣經》的技術,在中世紀的歐洲十分盛行。著名神學家奧古斯丁的《論基督教學說》是神學詮釋學的代表著作之一。在宗教改革時期,新教神學家們為了維護自己對《圣經》的理解,試圖用詮釋學工具對教會學說的獨斷傳統展開批判,神學詮釋學因此成為神學內一個不可缺少而具有漫長歷史的學科。語文詮釋學也最早出現在古希臘羅馬時代,當時的“批評法”就是一種簡單的語文詮釋學。經過法國古典主義到德國古典主義時期沃爾夫、邁耶等人的開創性努力,語文詮釋學在古代語法學和修辭學的基礎上發展為一種關于解釋和理解的方法學。
在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推動下,重新認識傳統的要求呼聲日起。無論是神學的詮釋學還是藝術領域內的語文詮釋學都面臨著同樣的處境。在人們對于自身“理性”的發掘和自信中,兩種傳統的詮釋學走向了統一。人們發現,沒有某種程度上對意義的解釋,就不能正確理解文本;沒有適當的文獻學訓練,就無法理解文本的信息。偏重于意義哲思的神學和重視修辭技術的語文學可以也應當合而為一。這種統一了的詮釋學,實際上是一種正確理解的技術,是一種狹義的關于文本解釋的方法論。
方法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科學,而非哲學 。方法論所討論的是人們在面對一項特定任務如何解決的問題,它不問這項任務本身的含義,更不管為什么要承擔這項任務。而哲學考慮的問題則遠為深邃,它要追問這項任務自身的意義和源流,這是哲學唯一關心的問題。“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在方法論和哲學的關系上,哲學乃是大“道”,方法論即便不屬于“器”的范疇,至多也是中“道”。詮釋學由方法論向本體論的轉變,是現代詮釋學最重要的發展階段。這一轉變標志著詮釋學進入了真正的哲學殿堂,為人們認識世界的本原提供了新的“視域”。
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是實現這一轉變的奠基者。施萊爾馬赫第一次從哲學的角度把詮釋學理論系統化,提出了“語法解釋”和“心理解釋”的概念。在他的研究中,重點是理解本身,而不是被理解的文本。因此,詮釋學不僅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也成為了一種認識論。狄爾泰在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深刻影響下,希望以“歷史理性批判”而使“精神科學”及人文科學關于人類歷史的知識,能夠像自然科學關于自然界的知識那樣確鑿可靠。在狄爾泰看來,詮釋學正是作為“精神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的學科,這樣他大大擴展了詮釋學的應用范圍,使之成為一種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論。普遍方法論再向前一步,就將成為哲學本體論的范疇。
20 世紀上半葉,海德格爾發起了詮釋學的根本性轉折——本體論轉向。畢生追尋“存在”之意義的海德格爾認為:“存在的意義必須以自身的方式展示出來,這不同于存在者被發現的方式”。 這一洞見直接導致了“詮釋現象學”的產生。在他看來,詮釋學正是追尋“存在”之意義的根本方法。詮釋現象學不是認識論和純粹的方法論,更不是分析描述的技術,而是一種本體論。本體論的詮釋學要解釋的不是古代文本或先哲的深奧語句,它指向的是存在,是古往今來的人類生存。
海德格爾的學生伽達默爾秉承了他的本體論轉變,把詮釋學進一步發展為哲學詮釋學。伽達默爾極力弱化詮釋學的方法論意義,而把詮釋學當作哲學本身來對待,認為詮釋學是人的世界經驗的組成部分。伽達默爾通過強調理解的普遍性,確立了詮釋學作為一種以理解問題為核心的哲學的獨立地位。“如果說海德格爾的詮釋學其最終目標是要探索存在的意義的話,那么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關心的則是人生在世、人與世界最基本的狀態和關系。”
至此,哲學詮釋學完成了從方法論到本體論的轉變。人們原來需要理解和把握的是一門理解的技術,而現在成為了理解理解本身。詮釋學也從昔日作為陪襯的“方法論”的暗淡色彩中脫穎而出,一躍而擁有了哲學領域中最耀目且最神秘的本體論的光環。然而,即使是哲學詮釋學在本質上也仍然擺脫不了方法論的意義,它在根本上是本體論,但絕不僅僅是本體論。從其發展源流上看,哲學詮釋學的本體論意義來自于方法論意義的不斷拓展和深入。哲學詮釋學的本體論意義不能否定其方法論意義。更何況,按照伽達默爾本人的“實踐”觀,或許更具實踐價值的正是在于詮釋學的方法論。
二、在語言的途中
語言是什么?這是個問題,而且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無論我們怎樣回答,我們都在用語言本身回答語言,這樣就陷入了自我解釋的循環。神學詮釋學的悖論與此有類似之處。上帝具有無限理性,上帝的話語是不能理解的,因此出現了以解釋上帝語言為己任的神學詮釋學,試圖將上帝的語言轉化為人類可以理解的語言。然而我們能夠相信這種解釋是真的可信么?它與上帝的本意相符么?如果上帝可以被解釋被理解,那么上帝還是神圣的上帝么?神學詮釋學的悖論就在于:上帝的存在應該為人理解,但是上帝本身是不能被理解的。
當然,語言的情況要樂觀一些。語言和上帝一樣,是自在的,也就是“道成肉身”。但相對于上帝,語言至少在形式上是有限的。在普遍語言的統一性和人類語言的多樣性中,能夠發現語言的可理解性。因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
語言的存在性又是什么呢?我在此稱之為語言的邏各斯,或語言的理性,語言之道。將這種邏各斯抽象并展現出來,即使語言的本體論與方法論。
施萊爾馬赫認為,詮釋學的一切前提不過只是語言。這個論斷開啟了伽達默爾以語言為中心和主線的詮釋學轉向運動。在《真理與方法》中,涉及三個部分的內容: 1 、藝術經驗里真理問題的展現; 2 、真理問題擴大到精神科學里的理解問題; 3 、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向。這三個部分分別構成三個領域,即美學領域、歷史領域和語言領域。實際上,盡管在這本書中不同篇章的標題各異,但它們最終幾乎都談到了語言問題。這決非偶然。“因為語言是使過去和現在事實上得以相互滲透的媒介。理解作為一種視域的融合本質上是一種語言學的過程。” 語言,無論作為理解的方法還是作為理解的本體,在詮釋學中都居于核心的地位。就此可以認為,哲學詮釋學的本體論和方法論,最終都體現并歸結為語言的本體論和方法論。
在希臘哲學中,語詞僅僅是名稱,并不代表真正的存在。名稱附屬于它的承載者,因而也屬于存在本身。語言的存在是相對的,是并非永恒且不確定的。柏拉圖就此指出,在語言中不可能達到實際真理,因此我們必須不借助于語詞而純粹從事物自身出發認識存在物。在柏拉圖那里,語言性只被說成是一種具有可疑的含糊性的外在因素。語言屬于突出自身的表面之物,真正的辯證法家必須對它棄置不顧。而在當時的希臘,也曾經發生過圍繞希臘青年的教育而進行的哲學和修辭學的斗爭,結果是關于語言的思維變成了一種語法學和修辭學的事情,開始把語言的意義域同以語言形態而出現的事物相分離。在對真理的無限追尋中,語言與作為“道”和“理性”的邏各斯分離了。
在文藝復興之后對于人類理性光輝的熱情追逐中,萊布尼茨提出了普遍語言的設想:通過某種符號系統的排列和組合,能夠獲得具有數學確定性的新的真理,因為由這樣一種符號系統所模擬的秩序將在一切語言中都找到一種對應。對于人類的理性來說,不存在比已知的數字序列還更高的認識恰當性。萊布尼茨所追求的語言理想是一種理性的“語言”,一種概念的分析。這種語言具有至高的理性,但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符號和工具。語言具有了“理性”的邏各斯,但還不是“道”的范疇上的邏各斯。在源流上,理性語言依然遵循著古希臘的傳統。
與這種語言和邏各斯分離的希臘傳統相反,基督教神學以“三位一體”的神秘性表明了語言之于世界的內在性。“精神的內在詞與思想完全是同本質的,就如圣子與圣父是同本質的一樣。” “語詞是純粹的事件(語詞真正來說是為人說話而創造的)。” 語詞與上帝同在,并來源于永恒性。這樣就把語言問題導回到了思想的內在性之中。基督教神學中的語言和邏各斯渾然天成,內在于思想的統一。
在某種程度上,基督教神學的語言觀已經接近了語言本體論。然而伽達默爾所實現的“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向”則更為明確的指出了語言的本體性。他借鑒洪堡“語言就是世界觀”的觀點,提出“語言并非只是一種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類所擁有的裝備,相反,以語言為基礎、并在語言中得以表現的乃是:人擁有世界。對于人類來說,世界就是存在于那里的世界……但世界的這種存在卻是通過語言被把握的。……語言就是世界觀。” 伽達默爾強調,語言是聯系自我和世界的中介,或者更正確地說,語言使自我和世界在其原始的依屬性中得以表現。
概而言之,語言的本體性所指的乃是:世界本身是在語言中得到表現。語言的世界經驗是“絕對”的。它超越了一切存在狀態的相對性,因為它包容了一切自在存在,而不管自在存在在何種關系(相對性)中出現。世界只有進入語言,才能表現為我們的世界。我們世界經驗的語言性限于一切被認為是或被看待為存在的東西。因此語言和世界的基本關系并不意味著世界淪為語言的對象,倒不如說,一切認識和陳述的對象乃是由語言的視域所包圍,人的世界經驗的語言性并不意味著世界的對象化,就此而言,科學所認識并據以保持其固有客觀性的對象性乃屬于由語言的世界關系所重新把握的相對性。這就是伽達默爾所謂的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向。
三、語言本體論的歷史學方法論意義
以詮釋學為先導,以語言的哲學本體論轉向為標志,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出現了一派新的氣象。人們在紛繁復雜的學問中終日忙碌,猛回頭卻發現他們的研究活動與研究對象之間原來還有一條未曾識見的巨大鴻溝,決定最終的“認識”正確與否的關鍵并不在于主觀的努力或是客體的真實,而是在于主客體鴻溝之間的那座橋梁——語言。正如荷爾德林的名言:“詞語破碎處,無物存在。” 語言的作用在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認識自我的過程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語言的哲學本體地位,決定了它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中的核心意義。歷史學的研究,也被卷入了這一大潮。
(一)詮釋學的宇宙
德國歷史學派曾經提出,不是思辨哲學,而只是歷史研究,才能導致某種世界史的觀點。不論是蘭克還是德羅伊森,他們都假定:理念、存在和自由在歷史實在中找不到任何完全和恰當的表現。但與此同時,德羅伊森也提出:“我們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使用實驗手段,我們只能研究,并且除研究外不能做任何別的。” 在這里,與自然科學相區別的研究是什么呢?伽達默爾認為,一定有另一種無限性不同于未知世界的無限性,這種無限性在德羅伊森眼里是歷史認識成為研究的主要標志。而如果要達到對這種無限性的有限認知,則只能通過詮釋學來實現。因此,“歷史學的基礎就是詮釋學。”
在伽達默爾看來:所謂歷史實在,永遠不可能進行自我認識。一切自我認識都是從歷史地在先給定的東西開始的,這種在先給定的東西,黑格爾稱之為“實體”,因為它是一切主觀見解和主觀態度的基礎,從而它也就規定和限定了在流傳物的歷史他在中去理解流傳物的一切可能性。而可以稱之為“實體”的東西,正可以看作為哲學詮釋學中的語言。毋庸置疑,語言作為詮釋學經驗的媒介,必然能夠在歷史學的研究中得到應用。
與當代語言分析哲學的看法相反,伽達默爾不認為語言是事物的符號,而認為語言乃是原型的摹本。符號本身沒有絕對的意義,它只有在同使用符號的主體相關時才有其指示意義,而且它的意義就是它所代表或指稱的事物。反之,摹本決不是原型的單純符號,它并不是從使用符號的主體那里獲得其指示功能,而是從它自身的含義中獲得這種功能,正是在摹本中,被描摹的原型才得到表達并獲得繼續存在的表現。
原型與摹本之間關系的比喻為理解歷史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德羅伊森曾經指出,連續性是歷史的本質,因為歷史不同于自然,它包含時間的要素。而按照哲學詮釋學的理論,理解不屬于主體的行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它標志著此在的根本運動性,正是這種運動性構成此在的有限性和歷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經驗。語言的表現形式——文字流傳物,包括藝術,其真理和意義永遠是無法窮盡的,而只存在于過去和現在之間的無限中介過程中。因此,視域融合不僅是歷時性的,而且也是共時性的,在視域融合中,歷史和現在、客體和主體、自我和他者構成了一個無限的統一整體。正如伽達默爾所舉的例子:“一尊古代神像——它不是作為一種供人審美享受的藝術品過去被供奉在神廟內、今天被陳列在現代博物館中——即使當它現在立于我們面前時,仍然包含它由之而來的宗教經驗的世界。這有一個重要的結果,即這尊神像的那個世界也還是屬于我們的世界。正是詮釋學的宇宙囊括了這兩個世界。”
在這里,從語言的本體論出發,我們對于歷史的認識顛倒了以往形而上學關于本質和現象、實體和屬性、原型和摹本的主從關系,原來認為是附屬的東西現在起了主導的作用。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通過語言媒介而進行的、因而我們在解釋本文的情況中可以稱之為談話的那是一種真正歷史的生命關系。理解的語言性是效果歷史意識的具體化。”
當人們一次次懷著對時間距離的敬畏,追問人類自身存在的秘密時,哲學詮釋學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視域”:我們不僅生活在世界上,也生活于歷史中;我們不僅生活在當下可觸摸的現實里,也生活在超越物質的關系中。我們不斷與世界發生關系,不斷與歷史發生關系,并將不斷與未來發生關系。語言是我們理解這些關系的鑰匙,或者說,語言就是這些關系。
(二)“語言轉向”哲學的史學回應
詮釋學所蘊含的哲學思潮對于史學的波及由來已久,影響深遠。在西方史學界,自蘭克之后的許多歷史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詮釋學中的一些思想。尤其是在歷史研究的方法論方面,在“語言轉向”說的引領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以福柯、懷特等人為代表的后現代史學派,對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展開了激烈的批判,為史學的發展開辟了若干條新的道路,他們手中所持的利器,正是來自于詮釋學,來自于語言的本體論。
前面已經提到,狄爾泰提供了一種關于精神科學的總的方法論。他認為:“理解和解釋是貫穿整個人文科學的方法。” 要獲得對歷史的認識,必須通過一條與自然科學相異、而與其他人文科學相同的道路才是可能的,這就是理解和詮釋。
詮釋學與歷史的緊密關系引發了西方歷史學家們的強烈關注,他們期待著能夠從這一新的哲學思潮中獲得對歷史的新的認知能力。后現代史學大師海登·懷特承認:“歐陸對歷史闡釋問題的興趣是由于普遍對解釋學發生興趣而發展起來的。”
余英時 先生曾把史學方法歸為兩類:一是“把史學方法看作一般的科學方法在史學研究方面的引申。”二是“指各種專門學科中的分析技術,如天文、地質、考古、生物各種科學中的具體方法都可以幫助歷史問題的解決” 。從西方史學后來的發展軌跡來看,尤其是從后現代史學的思想框架來看,詮釋學對歷史研究的方法論意義主要不在于微觀的研究技術層面,更多地集中向了如何認識“歷史”本質的問題。
無論是福柯的“知識考古學”還是懷特的“元歷史”,在后現代史學的研究中都把焦點對準了“認識歷史”的過程,而非以往歷史研究中重于一切的“歷史事實”。這一研究方向的確立,無疑深受了詮釋學和語言本體論的影響。“一個歷史敘事必然是充分解釋和未充分解釋的事件的混合,既定事實和假定事實的堆積,同時既是作為一種闡釋的一種再現,又是作為對敘事中反映的整個過程加以解釋的一種闡釋。”
大致說來,后現代史學理論的主要觀點如下:
• 對歷史現實的概念提出懷疑,認為歷史認識的客體不是獨立于認識者之外的實體,而是由語言和推論的實踐構成的。
• 認為語言不只是表達和交流的工具,而是形成意義、決定思維和行動的主要因素。因此,話語的形式在很多方面決定由它建立的文本的內容。這樣既對過去的歷史文本和當代的歷史敘述能否符合實際地構建過去提出懷疑,又向歷史學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們更深地理解歷史,更多地考慮客觀性標準和自己的文學創作。因為,歷史學家已不能滿足于讀懂史料,而要解讀史料所用的語言背后的意義。
• 由于抹殺了事實和虛構之間的界限,就對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懷疑。
• 對歷史認識的信仰和對客觀真理的追求提出懷疑。最終,對歷史學家的職業意識和職業主權提出懷疑。
詮釋學及其語言本體的轉向為后現代史學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歷史并不是一種客觀的“實在”,而是由語言編織起來的“存在”。歷史在本質上是一種語文的闡釋,帶有一切語言構成物的虛擬性。歷史的客觀性在后現代史學家那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所謂的“歷史”已經不是歷史本身,其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語言”。語言不僅是思維世界的本體,也成了物質世界的本體。
如果蘭克的歷史可以稱作“科學化的歷史”,那么我們不妨把后現代史學家們眼中的歷史稱之為“藝術化的歷史”。理性精神和科學主義主導了蘭克學派追逐“真實”的意識趨向,而詮釋學自身蘊含的非理性思潮和“形而上”的哲學性質則直接決定了后現代史學的“藝術化”。
二十世紀以來,這兩大截然不同的歷史研究陣營硝煙不斷,紛爭頻出,直到現在仍無法調和。有關他們的爭論,學界多有評介,無須贅述。臺灣學者 黃進興 先生的評述對詮釋學引入歷史研究的后果作了恰當的描述,頗為深刻:“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其理論涵蘊足以解消方法論的效度,造成歷史判準的困擾;法國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更直接質疑以往史學所預設的‘連續性',德里達、巴特提出‘文本'的觀點以解除作者的詮釋權,而憑讀者師心自用,推衍極致則可泯滅原始資料與間接資料的區別;此外,美國懷特更提出‘文史不分'的說法,導致虛構與史實最終竟無甚差別。”
四、治史之目的:“真實”還是“現實”?
(一)歷史研究的兩種動機
錢穆先生曾講到:“中國人觀念,古今一體。茍無古,何有今。今已來,而古未去,仍在今中。好古實即為好今。” 這段話很令人回味。
按西方傳統史學的看法,“古”即為歷史。然則以后現代史學的理論,“歷史”未必就是“古”,其由語言“編織”的性質而更接近于“今”。個人以為,后現代史學的弊端之一便是沿著語言本體論的哲學指向走往了極端。歷史是由時間序列形成的一系列事物的總和,這一點無可否認。語言的產生發展過程本身也是一個時間序列。歷史在本質上的確是一個人們無法改變的客觀實在,而非語言的產物。
然而,后現代史學又具有極深的洞見。蘭克學派的缺陷在于他們的史學和時代完全脫節。主要由于他們對于史學上所謂“客觀性”的問題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們假定歷史事實是百分之百的客觀的,可以通過科學的考證而還原到“本來面目”。如果一切事實都考證清楚了,那么全部的歷史真相自然會顯現出來。但是,歷史事實的“本來面目”又怎么可能完全重現呢?人們的認知能力終究是有限的,對未來如此,對過去同樣如此。
“歷史”的本質如此撲朔迷離,人們難以把握。事實上,討論這個問題的最大意義并不在于“歷史”本質的哲學價值。對歷史本質認識的分歧體現了歷史研究的兩種動機:一是求“真”,一是求“用。”研究歷史,究竟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過去的“真實”?還是要在某種程度上服務于“現實”?這才是歷史學家們最關心的問題。
中國的史學源遠流長,異彩紛呈。總的來說,中國傳統的歷史研究走的是“六經皆史”、“我注六經”的路子,更傾向于由“詮釋”來構成歷史。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早已觸及了歷史研究中主客觀對立與統一的辯證。在冰冷的歷史“事實”與生動的時代現實需要之間,中國史學家幾無例外地選擇了后者。“古代中國歷史學從來不避諱這種由于‘權力'與‘知識'關涉而形成的‘寫法',所謂‘春秋筆法'與‘美刺說',并沒有把‘真實'當作它的終極追求,它把書寫歷史當作一種獎懲的權力,同時也把權力的認同當作獎懲的依據。”
我們不能同意后現代史學將“歷史”視為現實中權力和語言的產物,但也不能完全抹殺“歷史”的“現實”性。歷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實,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詮釋。人們研究歷史,總是抱有某種目的的。即便是清代醉心于蟲魚之學的考據學派,埋頭故紙堆不問世事,卻也表明了他們對漢民族文化的深深眷戀和對異族統治的消極抗爭。 梁啟超 先生在早期曾提倡“史以致用”, 錢穆 先生言“好古即為好今”,沿襲的都是數千年來的中國傳統史學觀。
西方的歷史研究則生長在一片完全不同于中國的土壤中。從古希臘開始,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以后,自然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始終占據著西方文明的主導。對事物“本原”的探尋,在西方人眼里可以毫無其他任何的意義,只是為了求得“真”的認識。正是在這些思潮的長期浸染下,蘭克學派才可能獲得持續至今的生命力。中國近現代史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蘭克學派的影響。 梁啟超 先生后來倡導“新史學”,以及 傅斯年 先生的“史料學”,無不系從此出。
(二)“思想史”的后現代性
后現代史學一個重要的理論即“知識考古學”。在這一理論看來,歷史是人們主觀“后設”的,而非過去的事實“自設”。或者說,在后現代史學那里,歷史不過是人的“觀念史”,而非“歷史”本身。
在史學研究中,思想史在本質上也許最契合于后現代史學的描述。“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歷史記憶不僅是回憶那些即將被遺忘的往事,或是遺忘那些總是會浮現的往事,而且是在詮釋中悄悄地掌握著構建歷史、改變現在以控制未來的資源,各種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體,都是在溯史尋根,也就是透過重組歷史來界定傳統,確定自我與周邊的認同關系。”
由此可見,思想史更接近于一門“詮釋”的學問,研究者要對流傳下來的“文本”進行詮釋,而這些“文本”本身已經包含了當時作者對文本內容對象的詮釋。在這個意義上,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是應當肯定的。我們要想真正的理解“文本”的含義,必須謹慎地剝離掉覆蓋在“文本”上面的一層又一層的“詮釋”外衣。
中國的思想史畫卷中,以“詮釋”作為思想的產生、傳播方式的例子實不在少數。以經濟思想史為例。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質疑并挑戰封建社會三大經濟教條的思想隨處可見。而在這些寶貴的經濟思想中,更有多數是以對古代經濟觀點的重新闡釋而發表出來的。王符面對東漢時期“重本抑末”的思想教條的沉重壓力,重新詮釋了“本”“末”的概念,達到了反擊的目的。近代嚴復同樣采取了這種方式,他對傳統的“本末”、“奢儉”等范疇作了資本主義的解釋,以舊瓶裝新酒,很快得到了社會的認同。除此之外,康有為在考據學的外觀下,以辨別今、古文經真偽的方式,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啟蒙開辟了一條捷徑。
在某種程度上,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項“主觀”對“主觀”的研究。人們的主觀意識往往具有脫離社會現實的特征,或者超前,或者滯后,具有更大的偶然性。近現代中國史學有兩大學派:強調現實意義的“史觀”學派和強調歷史真實的“史料”學派。倘若我們思想史研究走的是哲學研究的路子,則“史觀”更重要;若是走歷史學研究的路子,則恐怕“史料”要更重要一些。但是無論如何,思想史終究是關于某些意識、觀念的軌跡的記載和詮釋。在這一點上,后現代史學更接近我們熟知的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和內涵。而后現代史學建立的哲學基礎或者說廣義的方法論基礎,正是根源于哲學詮釋學。
不止一位歷史學家在評論后現代史學時指出,對歷史客觀性的質疑有相當的合理性。但是這種理論的最大意義在于摧毀性,而非建設性。因為后現代史學在本質上是一種歷史哲學,討論的是“元歷史”問題。它們關注的是“歷史”這個概念的內涵,探尋的是何為“歷史”本體的哲學解釋。在后現代史學家們看來,歷史其實是個哲學問題,反映的是人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并與這個世界相處的關系。二十世紀初哲學詮釋學以及結構主義的巨大影響,深深地震撼了人們對理性、對知識的看法,重新審視“歷史”這門學科,只不過是這一潮流之下的一個方面。當人們對“科學”、“理性”等過分渲染人類主觀能動而導致人與世界“二元對立”的理念感到困惑和反感時,歷史學家們從詮釋學和結構主義那里得到了啟示。“語言”是連接人類認知與客觀世界的唯一橋梁,在人們有限的思維能力下,也只有將“語言”視為本體才是面對這個復雜的世界最心安理得的解釋。
也正是由于將“歷史”虛化,后現代史學家們很難把他們的理論應用到具體的歷史研究中去。其實,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的明白,歷史從來不可能“如實”地重現,從來都是經過“詮釋”處理之后的結果。人的理性和認識能力總是有限的,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明出“魔幻水晶球”或是“時空穿梭機”,人無法看到真正的“歷史”。那么,在這些現實條件的約束之下,盡可能地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因素的影響,盡可能地恢復“歷史”的原貌仍然是有必要的。更何況,“歷史學”的存在,有哪一天不是為了現實的需要而存在呢?詮釋學也好,后現代史學也好,它們對于歷史研究的貢獻,只是在于提醒人們不要過分地陷入主觀意識對于“歷史真相”的不自覺篡改傾向中去。這種警醒,對于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或許尤為重要。
The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Language Logos: the meaning to History and History of thoughts in studying Hermeneutics
Abstract : as a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deriving from some simplex explanative technology, Hermeneutic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 The value of methodology of modern hermeneutics is irrepealably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rmeneutics is a kind of ontology. Being the kernel of hermeneutics, Language was endowed with more significance in cognizing Nature, Society and Self. The trend of “Veering to language” aroused great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 realm. The philosophy bedrock of Post-modern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it. Some viewpoints of Hermeneutics and Post-modern History should be absorbed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or history of thoughts in order to get a balance between the “Real” and “Now”.
Key words : Hermeneutics; Veering to language; Post-modern History; History of thoughts
一般認為,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是構成哲學體系的三個分支。考慮到人類思維活動的層次特征,本文作者傾向于將方法論作為區別于本體論這一哲學根本目的的較低層次的知識體系。
《易傳.系辭》,第十三章
海德格爾 : 《存在與時間》,倫敦 1962 年,第 26 頁
劉放桐等 : 《新編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495 頁
海德格爾,《在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 1997 年
〔德〕 H-G.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下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615 頁
〔德〕 H-G. 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夏鎮平 宋建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20 頁
〔德〕 H-G.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下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546 頁
托馬斯,《神學大全》,第 1 部,問題 34 及其他地方
〔德〕 H-G.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下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574 頁
荷爾德林,《面包和酒》,載于 1919 年《藝術雜志》 11 、 12 期
轉引自:〔德〕 H-G.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下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280 頁
〔德〕 H-G.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下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258 頁
〔德〕 H-G.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下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6 頁
〔德〕 H-G.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下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503 頁
《狄爾泰全集》第 7 卷,第 138 頁
海登·懷特,《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 張萬娟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第 64 頁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轉引自《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5 年,第 11 頁
一旦涉及到“本質”問題,任何研究都容易演變為哲學的討論。后現代史學家們倡導的“元歷史”概念之所以被批評為“空洞無物”,根源就在于他們所采取的方法論,本來就始自于哲學的本體論。
海登·懷特,《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 張萬娟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第 63 頁
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轉引自《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5 年,第 41 頁
錢穆,“略論中國考古學”,《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三聯書店, 2002 年,第 159 頁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131 頁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9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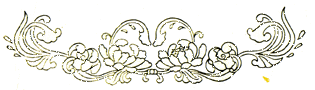
![]() guoxue@guoxue.com
guoxue@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