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輯發稿之際,京城正大鬧燥熱,直鬧得流金爍石發昏發狂。倒是密云這邊尚余幾分清涼,裝好的空調也使不上,益顯得城里的熏蒸多是人禍。
此種對比,更惹人發思古之情。論文一欄里,陳來和吳震的文章,分從內部和外部,潛回了當年王學的語境。前一篇處理會講活動,認為它既是王學知識人的交往形式,又是理學下滲的傳播形式,既與地方風俗教化相關,更體現了思想與實踐的互動;由此可窺知王學作為跨地域話語體系的形成條件,及其深入社會文化的某些機制;作者準此提示,中國文化的同質性在宋以后已大為提高,故對思想話題似不宜區域分割。后一篇處理“現成良知”命題,認為它既強調了良知存在的先天性,又強調了其顯在性,此一點又與其遍在性不可分割:正因其無時不在現象世界中發用流行,對之的把握就須“即用求體”,亦即在已發世界、現實生活中把握良知本體。
與此相映,費格爾和霍倫斯坦分別研討了西方傳統,這種思想考古還蘊含了未來的展望。前一篇展示了德國哲學的自我克服路徑:為了滿足想在與自身的協調一致中行動的理性的人的自我要求,強調普遍形式律令的康德倫理學在完成自我立法的同時也顯出了矛盾;正是此類矛盾催生了席勒有關審美中介的著名論說,使人有可能在感性層次上考慮道德自由,并將觀念倫理學和責任倫理學的立場聯系起來。后一篇展示了同一哲學譜系的另一番批判繼承:盡管雅斯貝爾斯并不贊同黑格爾作為絕對精神漫游的人類文明史的單一演進路線,卻驚人地接近黑氏的問題設定,而認定人類是一整個超越所有時代、所有大陸、各種進化樣態的理解和交往共同體;在以現代知識成就應答雅氏的基礎上,作者又以對“人類史前文明史”的重構承襲了其文化普世主義,并藉科諾羅索夫對瑪雅文字的破譯示例:盡管并無發生論上的親緣關系,瑪雅、埃及和中國的文字間仍存在結構上的可比性。
接下來兩篇來自社會科學。王國斌在比較歷史學的視野中,生發出修正現有社會理論的企求:他以中西都有的“福利制度”和舶入中國的“公民”與“政治參與”為例,說明基于歐洲經驗的理論往往不能分析其他社會的實際變化,所以社會理論應放棄對歷史變遷之大規模復雜聯系的簡單設想,而建立小規模變化的微觀研究典型,以探尋特殊背景下各變化間的關聯,更好地把握復雜的歷史動力和未來的政治可能。史國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試圖解答臺灣的另一個奇跡:快速的工業化何以并未伴隨類似歐美和其他國家以工會為基礎的對立勞工關系?作者給出了三點具體答案,包括制造商善于在工廠里以文化意識形態等手段來營造認可;但作者又指出,工人對當前勞工制度的不滿也表明:一旦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勞工問題也會隨之產生,工人的階級意識或會比其敵對勢力更強。
最后兩篇論文涉及道佛二家。伍曉明試圖通過詳盡的概念分析和文本詮釋而對《老子》第一章做出哲學新解,以表明老子的思想仍然在我們“面前”而非已留在“身后”;作者要重新體驗老子文本的真正“語言”力量,以為中國傳統與西方思想的真正有基礎的“面對”開辟可能。曹虹以何無忌就僧人袒服之習向慧遠質疑為案例,凸顯了佛教向社會生活滲透、與本土思想合流時難以避免的文化問題。
評論一欄,龔雋評介了1980年代日本佛教學者谷憲昭和松本史郎發起的“批判佛教”運動,既肯定其對“禪與基礎主義”的說明,又指出其夸大語言與邏輯在佛教中的地位,否定禪宗的超驗性,會帶來許多難以解釋的困難。作者還梳理了批判佛教的方法論,認為它其實是在檢討韋伯“價值中立”的學術立場,而自身又蛻變為一種主義的宣傳。林悟殊從金石學、語言學、神學、宗教史等多個角度,綜述了三百多年來圍繞西安景教碑的研究,并系統整理了國內、法國、日本、港臺等學者關于碑文內涵解讀、文物出土、樹碑原因等方面的各派學說。
書評一欄,本輯的份量尤重,此處只能略舉兩篇:其一是張伯偉對《程千帆文集》各卷的逐一評述,我們以此悼念這位剛度完了輝煌晚年的學長;其二是吳承明對《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反思,相信此書雖已介紹過,吳老的學力仍會使人眼前一亮。
通訊一欄:唐曉峰基于形勢圖和實用圖的古代區分,展現了傳統地理文化的豐富側面,和由理想和實際共同織就的帝國秩序,藉此回應了上輯葉凱蒂的文章。這種懇談般的切磋,使人油然想起開頭陳來文章中的先賢語錄:“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惟愿至少在《中國學術》這里,此種古風尚不致滅絕!
劉東
二○○○年八月一日于京郊溪翁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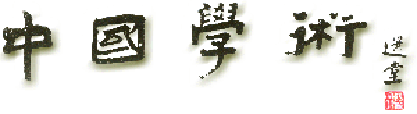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