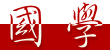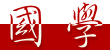|
□金克木
鑒真和尚現(xiàn)在是中日友好中的著名古人了。我想從有關(guān)他的一件事談起,談一些與他無(wú)
關(guān)的話;并不是想湊熱鬧或押冷門,只是讀書有感提供參考。
九十九年以前,即1881年,英國(guó)牛津出版了馬克斯·穆勒校刊的《日本所得佛教典籍》
第一本,《金剛能斷》即《金剛經(jīng)》的梵文原本。本文前面有校者敘述獲得幾種梵本的經(jīng)過(guò)
。他先在1879年從日本得到《(小)阿彌陀經(jīng)》,在1880年校刊于英國(guó)亞洲學(xué)會(huì)會(huì)刊,隨即又
得到這部《金剛經(jīng)》和《心經(jīng)》和唐朝義凈的《梵語(yǔ)千字文》等等。還有日本收藏的用柬埔
寨字母和緬甸字母書寫于貝葉的巴利文佛經(jīng)以及僧伽羅文片段等寫本。在這篇文中有一段是
:
“短的陀羅尼,名為《尊勝小心咒》,是抄寫本,原件為涂銀的深藍(lán)色紙,是著名的中
國(guó)和尚鑒真所寫,他于公元753年到日本,成為律宗的建立者。原件屬鑒真所修建的唐招提
寺,在大和的奈良。”
后面列舉日本所藏梵本時(shí)又有一段說(shuō):
“唐招提寺,在大和的奈良:深藍(lán)色紙,銀字書寫,其中有公元753年到日本建立這寺
的鑒真所寫的陀羅尼;由兼松和太田抄錄來(lái)。還有些咒語(yǔ)也在同一卷寫本中,沒(méi)有抄來(lái)。”
這是有關(guān)鑒真的兩段話。此外還有關(guān)于中國(guó)和日本的一些和尚將梵本傳到日本的記載。
這部《金剛經(jīng)》的校刊依據(jù)共有四個(gè)本子,在書中各附書影一張。一是直行,有悉曇字
母的梵文原文,漢字譯音,漢文直譯,鳩摩羅什漢譯,達(dá)磨笈多漢譯,五種并列對(duì)照。二是
只有梵文,與上一本同出一源。三是俄國(guó)圣彼得堡的帝國(guó)科學(xué)院所藏的西藏木刻印本,橫行
,有梵文原文,藏文音譯,藏文譯本,并列對(duì)照。藏譯已在1837年校刊。四是從北京得到的
木刻<SPS=1271>紅印本,橫行,只有原文。由此,校者馬克斯·穆勒認(rèn)為中國(guó)必尚藏有很多
佛經(jīng)梵文寫本。
《金剛經(jīng)》梵本刊行后,《日本所得佛教典籍》第二本在1883年刊行,是《無(wú)量壽經(jīng)》
附《阿彌陀經(jīng)》。馬克斯·穆勒在序中說(shuō)曾見(jiàn)到中國(guó)創(chuàng)辦金陵刻經(jīng)處的楊文會(huì)(楊仁山),托
他回中國(guó)訪求梵本。九十幾年來(lái),我國(guó)果然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大量梵文寫本。不但佛教經(jīng)典,還有
其他,也不只梵文一種語(yǔ)言的文獻(xiàn)。例如德國(guó)人從新疆吐魯番得去的一些殘破的寫有梵文的
貝葉就在1911年由呂德斯校刊出來(lái),原來(lái)是三部宣傳佛教的戲劇殘本。這在印度文學(xué)史上算
是一件大事。隨后,西藏收藏的梵本也在國(guó)際上知名了。印度的羅喉羅(他著重的是梵文論
藏)和意大利的杜奇(他著重的是圖像和梵藏文本)都得了些攝影(羅喉羅),甚至原物(杜奇)
。這些都在印度、歐洲、美國(guó)、日本陸續(xù)刊印中。此外還有不少在印度及其他地方的佛教經(jīng)
典梵文本也不斷校印出來(lái)。當(dāng)然,沒(méi)有校印而尚在收藏中的數(shù)目更多。美國(guó)有個(gè)圖書館在搜
羅這類寫本,縮微收藏,供人利用。
1949年全國(guó)解放以前,我國(guó)文物流出國(guó)外的究竟有多少,是些什么,恐怕沒(méi)有全面調(diào)查
和統(tǒng)計(jì)的目錄。單是從一個(gè)敦煌流落出去的古籍?dāng)?shù)量就不少。不說(shuō)弄回來(lái),至少弄個(gè)目錄出
來(lái)吧。不說(shuō)“文物”,就只管“文”吧。有志于此并且為之努力者,我接觸到的有鄭振鐸、
向達(dá)、王重民、陳夢(mèng)家。不幸——這四位確實(shí)是都遭遇了不幸——他們都去世了,想做的事
都沒(méi)有完成,真可痛惜。我們現(xiàn)在想知道海外流落的我國(guó)文物,還是多半只得向外國(guó)去找信
息。當(dāng)前國(guó)際上圖書館和博物館都已逐漸以現(xiàn)代技術(shù)聯(lián)成了一片又一片的網(wǎng),調(diào)查以至復(fù)制
、縮微,技術(shù)上比從前應(yīng)當(dāng)是容易得不知多少倍了。何況我們目前首先需要的只是已刊出和
未刊出的中國(guó)古籍目錄(文物中“物”比“文”更難得),難道這也要外國(guó)人替我們做嗎?難
道在外國(guó)已經(jīng)做了的各種中國(guó)善本目錄,我們也不能有一全份供有關(guān)研究者參考嗎?
以上這段話已經(jīng)是題外了,下面還想講幾句離題更遠(yuǎn)的話。
近些年來(lái)國(guó)際上研究中國(guó)比以前所謂漢學(xué)研究大有不同了。1904—1924年法國(guó)人編的《
漢學(xué)書目》五卷共有4427頁(yè)。1958年袁同禮在美國(guó)刊出的續(xù)編有729頁(yè)。1964年英國(guó)出版的
漢學(xué)論文索引有578頁(yè)。1978年美國(guó)出版的關(guān)于“近代中國(guó)社會(huì)研究”的目錄有三冊(cè),就書
目本身說(shuō),歐洲語(yǔ)的540頁(yè),日本語(yǔ)的354頁(yè),漢語(yǔ)的590頁(yè)。這僅僅是一個(gè)方面的著述目錄
。究竟別人研究了我們的什么,出版了什么研究資料,難道我們不應(yīng)當(dāng)知道而且不斷了解新
的情況嗎?這也能一直靠外國(guó)人編目給我們看嗎?
從鑒真?zhèn)麒蟊菊勂穑呀?jīng)談到離題萬(wàn)里了,可是我還想多走一點(diǎn),也許是繞回了原地。 馬克斯·穆勒在校刊《金剛經(jīng)》的序文末尾說(shuō)了這樣一番話:“中國(guó)佛教徒能得到足夠
的梵文知識(shí),和印度佛教徒談?wù)摬⑶覐乃麄儗W(xué)習(xí)佛教玄學(xué)的含意,這真是個(gè)奇跡。同樣令人
驚奇的是,印度佛教徒竟能學(xué)會(huì)中文以至于能夠在那種語(yǔ)言中找出佛教及其哲學(xué)的抽象哲學(xué)
術(shù)語(yǔ)的準(zhǔn)確翻譯。就我所見(jiàn),我懷疑即使是最好的中國(guó)學(xué)者從即使是最好的譯者的譯本中能
得到《金剛經(jīng)》或類似的書的準(zhǔn)確理解,除非是他們能先讀梵文的原本。我的兩個(gè)學(xué)生(按
:指日本的南條文雄和笠原)這樣作了以后,常常發(fā)現(xiàn)能更好地理解玄奘等人當(dāng)初想表達(dá)的
意思,而在這以前他們似乎不能從漢譯發(fā)現(xiàn)確切的可譯出的意義,盡管他們對(duì)經(jīng)文差不多都
能背誦。”這位學(xué)者由日本和尚幫助得到梵本,又靠漢譯把它校刊出來(lái),又照他所了解的原
文譯成英文,收在他主編的《東方圣典叢書》中。
不管他的了解如何,他這段話不無(wú)道理。漢譯佛教文獻(xiàn)仿佛是原文的復(fù)制品,確實(shí)還不
如原文易讀;從原文確可以更好理解譯文,對(duì)照讀來(lái)別有意趣。我們講了一千幾百年的佛學(xué)
,多半是中國(guó)佛學(xué);究竟原來(lái)印度人講的什么,怎么講的,現(xiàn)在原書陸續(xù)出來(lái)(巴利語(yǔ)的早
已刊行全藏),應(yīng)當(dāng)可以重新用現(xiàn)代人能懂的話講講,由此也可對(duì)照出古代中印譯者以及譯
本的長(zhǎng)處和短處。這不僅是文獻(xiàn)整理工作,更不是“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是從這里面可以作
宗教的(中印佛教異同),哲學(xué)的(中、印、西方文化思想異同),語(yǔ)言學(xué)的(不同語(yǔ)系的梵文
和漢文、藏文如何對(duì)譯的潛在語(yǔ)言關(guān)系)研究,而且這還對(duì)于了解當(dāng)前印度及一些鄰國(guó)的民
族社會(huì)心理和民情風(fēng)俗等不易隨經(jīng)濟(jì)制度迅速改變的部分意識(shí)形態(tài)也會(huì)有所幫助的。可是話
說(shuō)回來(lái),宗教典籍可否有選擇有分析地出版呢?古籍刊行社出版過(guò)《百喻經(jīng)》,大概因?yàn)槟?
是魯迅印過(guò)的。宗教的書中有些是史料、文獻(xiàn)、哲學(xué)論著和文學(xué)作品,并不都是鴉片。宗教
書未可與宗教等同,老子的《道德經(jīng)》是道教經(jīng)典,并不等于道教。教理和教會(huì)是有區(qū)別的
。我這樣說(shuō)是否有為毒品辯護(hù)之嫌呢?
真是扯得太遠(yuǎn)了。如果《讀書》能發(fā)表以上這些文不對(duì)題的廢話,一定要請(qǐng)讀者諒解我
的本意不過(guò)是想提供點(diǎn)知識(shí)而已。正是:
鑒真東渡;梵本西行;九十九年,一彈指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