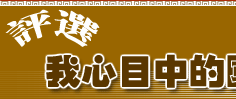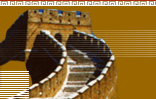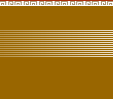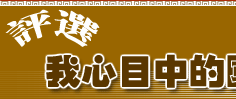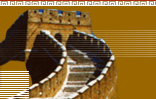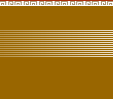上個(gè)世紀(jì)九十年代初,以《學(xué)人》的出版為標(biāo)志,“學(xué)術(shù)史”研究漸成顯學(xué)。近幾年來,隨著“國學(xué)熱”的興起,被現(xiàn)當(dāng)代中國歷史湮沒已久的不少著名學(xué)者,由于學(xué)術(shù)史研究探根溯源之功,紛紛從人們的記憶深處泛起,重新引起學(xué)術(shù)界、出版界乃至傳媒的注意。國人與傳統(tǒng)文化隔絕過久,加之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日益發(fā)煌,于是,一般被視作“國粹”之精粹的國學(xué)地位日高,自然不難理解。在此大背景之下,上述這些“出土”學(xué)者的精神取向、學(xué)術(shù)師承、專業(yè)分野、治學(xué)方法等等方面,卻未及得以仔細(xì)考辨,而被世人競相一律冠以“國學(xué)大師”的稱號(hào)了。
“國學(xué)大師”其逝矣,后來傳承衣缽的托命之人何在?這就不能不成為人們極度關(guān)心的問題。近來,國內(nèi)不少大學(xué)熱衷于開辦“文科基地班”、“國學(xué)班”甚至“大師班”,正是這種迫切心情的反映。這些“班”舉辦亦有年矣,其成效如何,實(shí)在難說。但我總相信,預(yù)其役者的心里應(yīng)該是明白的。在我看來,即使不能說這類“班”都是失敗的,那么,起碼也是與開設(shè)這些“班”的初衷和理想值相距甚遠(yuǎn)。這個(gè)判斷當(dāng)然只是我個(gè)人的管見,若要反駁卻也并不見得那么容易。
最近的說法似乎又有所改變。據(jù)一所名校的“國學(xué)院”主事者說,之所以要開設(shè)“國學(xué)班”,乃是為了滿足一些大公司的急切需要。據(jù)說,很多大公司對(duì)“國學(xué)班”畢業(yè)生極感興趣,熱烈歡迎他們?nèi)蘸笄巴吐毠ぴ圃啤?duì)這些不知所云、不明所謂的妙語,我真不知道應(yīng)該如何回應(yīng)。所以,我只能這樣回答屈尊前來采訪我的記者:
國學(xué)的寬泛化,的確體現(xiàn)了現(xiàn)在的人們對(duì)歷史、對(duì)祖先的關(guān)切,希望能領(lǐng)悟感受自己所屬民族的文化之根和血脈。但對(duì)于“普及國學(xué)”、培養(yǎng)“國學(xué)大師”這些做法,我的看法是“其心可佩,其志可嘉;想法可笑,效果可疑”。——每個(gè)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學(xué)”,雖然也會(huì)面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沖突,但至少是連續(xù)的,而我們斷裂得特別厲害。現(xiàn)在要說什么國學(xué)的“承前啟后”、“發(fā)揚(yáng)光大”是不可能的,我看只能“守先待后”。
這些話委實(shí)既不豪又不壯,必定會(huì)有不少“有志之士”不以為然。然而,我這么說,卻也有我的理由。最要緊的還是應(yīng)該真正地弄明白“國學(xué)大師”究竟是怎樣培養(yǎng)出來的吧。這當(dāng)然是個(gè)極大的課題,絕不是一篇短短的隨筆就可以說清楚的。還是來看看兩個(gè)例子吧。
一個(gè)例子是一個(gè)人,且并不是離我們非常遙遠(yuǎn)的古人——周一良先生(1913/1/19 —2001/10/23)。他的國學(xué)根底在學(xué)界無人不佩服。周先生在哈佛大學(xué)取得博士學(xué)位,但其深厚的國學(xué)功底主要是得自8歲起在名師執(zhí)教的家塾就學(xué)十年的這段經(jīng)歷。當(dāng)年的“一良日課”是這樣的:
讀生書:禮記、左傳
溫熟書:孝經(jīng)、詩經(jīng)、論語、孟子
講 書:禮(每星期二次)
看 書:資治通鑒(每星期二四六點(diǎn)十頁);朱子小學(xué)(每星期一三五點(diǎn)五頁)(同用紅筆點(diǎn)句讀如有不懂解處可問先生)
寫 字:漢碑額十字(每日寫);說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須請(qǐng)先生略為講音訓(xùn);黃庭經(jīng)(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紙景寫二月
請(qǐng)問,今天還有多少人真切地了解“讀、溫、講、看”的區(qū)別?當(dāng)時(shí)在周家執(zhí)教的古文字學(xué)大家唐蘭先生盛贊少年周先生“其人少年,學(xué)有根柢”。“根柢”實(shí)不同于今天泛泛而談的“基礎(chǔ)”,蓋前者重縱深,后者重平面,正是中國傳統(tǒng)世家式精英教育與現(xiàn)代普及式大眾教育分野之所在。這種教育的功過是另外一個(gè)問題,但是對(duì)于培養(yǎng)國學(xué)大師是切實(shí)有效的。著名歷史學(xué)家田余慶先生在《周一良先生周年祭》里非常平實(shí)地提到:“周先生還送過我?guī)追N古籍,其中《封氏聞見記》二冊是他親手校勘過的,從書尾所記干支看,是他二十出頭所讀。這樣的讀書方法跟今天的‘短平快’的讀書相比,可以看出不同年輩的人其國學(xué)根底的差異。”就是明證之一。劉成禹《世載堂雜憶》將教育模式分為“俗學(xué)”、“崛起”、“世家”三類,自有其深意。雖說也不是沒有例外,雖說國學(xué)大師不必盡是世家出身,但是,世家的教育模式、文化氛圍,更有益于培養(yǎng)真正的國學(xué)大師,卻也是不爭的事實(shí)。時(shí)至今日,世家或者世家式的教育早已灰飛煙滅。正可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再一個(gè)例子是機(jī)構(gòu),就是鼎鼎大名的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離我們也并不太遠(yuǎn)。在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上,成功地在很短的時(shí)間里,“批量”培養(yǎng)出符合或者接近“國學(xué)大師”標(biāo)準(zhǔn)的人才的機(jī)構(gòu),這是惟一的一家。研究院本身已是一個(gè)熱門的學(xué)術(shù)課題了,孫敦恒先生編著的《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史話》堪稱標(biāo)準(zhǔn)著作,有心人自可參看。別的不必說,從由吳宓、王國維等先生起草的《研究院章程》來看,它的宗旨簡單明了:“研究高深學(xué)術(shù),造成專門人才”;目的樸實(shí)明確:“目的專在養(yǎng)成左列兩項(xiàng)人才:(一)以著述為畢生事業(yè)者。(二)各種學(xué)校之國學(xué)教師。”
《研究院章程》之六“研究方法”更是精義畢現(xiàn):“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xué)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gè)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dǎo),其分組不以學(xué)科,而以教授個(gè)人為主,期使學(xué)員與教授關(guān)系異常密切”;“教授所擔(dān)任指導(dǎo)之學(xué)科范圍,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學(xué)之心得,就所最專精之科目,自由劃分,不嫌重復(fù);同一科目。盡可有教授數(shù)位并任指導(dǎo),各為主張。”“教授學(xué)員當(dāng)隨時(shí)切磋問難,砥礪觀摩,俾養(yǎng)成敦厚善良之學(xué)風(fēng),而收浸潤熏陶之效。”而擔(dān)任專任教授的“宏博精深、學(xué)有專長之學(xué)者”正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這已是久播于學(xué)人之口的了。
有斯院,有斯師,而有斯才,正此之謂。
發(fā)愿培養(yǎng)“國學(xué)大師”的主事者,是否也可以參考一下上面的兩個(gè)例子呢?只要稍微熟悉一點(diǎn)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史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例子是不在少數(shù)的。今天,大概在經(jīng)費(fèi)的充裕方面,或許和過去尚有可比,敢問其他呢?還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