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引用一段劉永華博士的話(huà)(見(jiàn)6月1日《新京報(bào)》),雖然羅嗦了一些,但能夠看出劉博士的邏輯和底牌:“‘生活哲學(xué)'通俗地說(shuō)就是我們?cè)趺纯创睿趺刺幚砩钪械男∈隆>灰?jiàn),有人喜食野味吃出了非典,有人貪污腐敗包二奶,有些文化人被人稱(chēng)為‘沒(méi)文化',有些政府官員只會(huì)兩件事:喝酒、打撲克。這些現(xiàn)象都反映了當(dāng)代中國(guó)‘生活哲學(xué)'
的普遍缺失,而‘國(guó)學(xué)'的精華部分,對(duì)這些現(xiàn)象都有針對(duì)性的規(guī)則存在。可以說(shuō),現(xiàn)在提倡‘國(guó)學(xué)'是時(shí)代發(fā)展的需要,是建設(shè)和諧社會(huì)的需要,既應(yīng)該研究,更應(yīng)該弘揚(yáng)。”
這段話(huà)的邏輯其實(shí)很簡(jiǎn)單,就是一個(gè)三段論:一、社會(huì)上出現(xiàn)了一些“不良”現(xiàn)象(姑且不論劉博士列舉的諸多“不良”是否具備科學(xué)性);二、針對(duì)這些“不良”現(xiàn)象,“國(guó)學(xué)”的精華部分設(shè)置了一些規(guī)則(姑且不論“國(guó)學(xué)”的精華部分究竟是頸部還是臀部);三,所以,提倡“國(guó)學(xué)”是時(shí)代的需要。
劉博士的意思是,“國(guó)學(xué)”能夠解決很多問(wèn)題,諸如SARS等醫(yī)學(xué)問(wèn)題,包二奶等家庭問(wèn)題,腐敗、政府官員效率低下等行政問(wèn)題。“國(guó)學(xué)”既然如此偉大,那么,我們對(duì)于“國(guó)學(xué)”應(yīng)持的態(tài)度,就不應(yīng)該僅僅是研究和弘揚(yáng)的問(wèn)題,也不應(yīng)該僅僅是在一所大學(xué)里設(shè)置系科的問(wèn)題,而是應(yīng)該詔告天下,傳布四海,人手一套《四庫(kù)全書(shū)》或者《十三經(jīng)》……如此這般,天下太平,馬放南山。
會(huì)這么容易嗎?在唐宋元明清,全部國(guó)民人手一套《四庫(kù)全書(shū)》或者《十三經(jīng)》不可能辦到,但所有官員以及文化人,人手一套《十三經(jīng)》或者《四書(shū)五經(jīng)》還是基本實(shí)現(xiàn)的。然而,疫病照舊流行,納妾仍舊成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貪污與腐敗照樣是官員的營(yíng)生。唐宋元明清,正是 “國(guó)學(xué)” ———或者說(shuō)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與文化———如日中天的時(shí)候,國(guó)家的運(yùn)作以神道化的儒教為根本,官員的考核以儒教宣揚(yáng)的道德為依據(jù),儒家經(jīng)典(這是否就是劉博士口中所說(shuō)的“國(guó)學(xué)”的精華部分的一部分?)成為萬(wàn)民的生活準(zhǔn)則。那些時(shí)代,“國(guó)學(xué)”一統(tǒng)江湖,千秋萬(wàn)代,并不存在繼承和弘揚(yáng)的問(wèn)題,然而,社會(huì)依舊是社會(huì),“不良”依舊是“不良”。
西諺有云,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說(shuō)的是一個(gè)邊界的問(wèn)題———每個(gè)人、每種知識(shí)、每種思想和文化,都有著自己進(jìn)退舉止的范圍。孔夫子說(shuō)過(guò)君子不逾距,也說(shuō)過(guò)進(jìn)退有度。這個(gè)“矩”和“度”,固然隨著時(shí)代的變化而不同,但其本質(zhì)是一樣的,就是該知道邊界在哪兒。“國(guó)學(xué)”的問(wèn)題、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和文化的問(wèn)題,在學(xué)術(shù)的范圍內(nèi)、在小圈子里討論,有其價(jià)值和意義;然而,一旦超越了這個(gè)“邊界”,像劉博士建議的那樣,以“國(guó)學(xué)”防SARS、反腐敗,只能是一個(gè)笑話(huà)。
然而,劉博士的意圖恐怕不僅局限于SARS和腐敗問(wèn)題:“‘國(guó)學(xué)'的精華部分,對(duì)這些現(xiàn)象都有針對(duì)性的規(guī)則存在。”這句話(huà)的要害在于“規(guī)則”二字,以“國(guó)學(xué)”中設(shè)立了數(shù)千年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和行為規(guī)范,應(yīng)用于21世紀(jì)的中國(guó),作為國(guó)民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和行為規(guī)范,甚至更進(jìn)一步,以弘揚(yáng)“國(guó)學(xué)”為由而限制國(guó)民自由思想和自由行為的權(quán)力———這種局面,在“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以來(lái)的中國(guó),并不陌生。這,恰恰是劉博士的底牌。
固然,當(dāng)下的時(shí)代不是一個(gè)盡善盡美的時(shí)代,存在著許多問(wèn)題。這些問(wèn)題,需要細(xì)致分析,逐一制定對(duì)策和解決方案。將所有問(wèn)題歸于國(guó)民的思想和文化出了問(wèn)題,進(jìn)而為其開(kāi)出一個(gè)一攬子藥方,實(shí)在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把“國(guó)學(xué)”局限在學(xué)術(shù)內(nèi)研究和學(xué)習(xí),作為國(guó)人,是有必要的,可以知道過(guò)去的中國(guó)人怎樣生活和思想,以史為鑒。然而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我們需要知道,“國(guó)學(xué)”是過(guò)去的學(xué)問(wèn),是已死的知識(shí),不是從當(dāng)下中國(guó)的實(shí)際中生發(fā)出來(lái)的鮮活的知識(shí),更不是江湖郎中宣揚(yáng)的靈丹妙藥,包治百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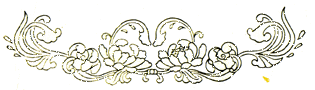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