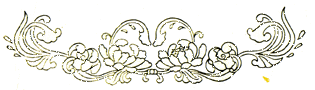| 筆者沒有見過哪個國學人士,要為借來的西方學術設定償還期。看來到時候是還不起的。那么,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把不得不“借”的東西“要”過來,變成自己的財產呢?
中國人民大學 成立了國學研究院 ,計劃要每年招20-30名6年制本科、碩士連讀的學生 ,雄心不可謂不大。 ,雄心不可謂不大。
這一研究院的目標,顯然是要振興中國傳統文化了。但看看其對國學的定義,卻不免有幾分糊涂:“國學指近代以來借鑒西方學術、理論、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進行研究和闡釋的一門學問”。
這個定義,好像很開放,其實卻很狹隘。說開放,是指其所謂借鑒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國的學問,不是用中國的方法來研究之說。用很時髦的話來說,這恐怕是所謂西方“文化霸權”的又一個例證了吧。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像筆者這樣在美國的大學里吃中國學問這碗飯的人,倒像是比國內的鴻儒名宿更為正宗。這實在有些讓人不敢當了。
不過仔細一想,這樣的開放精神又有些滑稽。我們常常說“借鑒”西方。為什么不說“采用”呢?這很能反映我們的文化心理。現在我們談中國文化,不借鑒西方的語匯幾乎沒有辦法談下去。
去年筆者與幾個文化保守主義者就 讀經問題展開過一輪辯論 。唇槍舌劍之后,很認真地探求過一番對方的文化底蘊。結果發現,對方雖然口口聲聲中國傳統文化,但真正“當家的”,不是孔孟之道,而是哈耶克、伯克等人。你讀他們的文本就能看出來,他們一引這些外國人的話才理直氣壯。既然如此,還讀經干什么?大家讀哈耶克、伯克不是挺好嗎?其實后來所謂的“ 文化霸權 ”一詞,也是西方學術界的產物。
這樣的窘境,說明我們其實很難把中國的現代文化從西方文化中清楚地區分開來。但國學派的許多人士,包括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似乎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抵賴自己是誰,一定要為自己界定出一個中國的文化精神,找出一些自己獨有別人卻沒有的東西。可惜不管怎么界定,自己身上的“洋味兒”就是去不掉,離開人家的語言就話也說不清楚。于是,國學為了區別于傳統學術,干脆稱自己是“借鑒”西方的方法,為自己使用外來的詞匯增加一些合法性。
妙就妙在這個“借”字。
顧名思義,“借”來的東西是一定要還給人家的。筆者小時候向父母要錢,明知道不會還,就干脆說“要”,不說“借”。等有了工作,具有償還能力后,才有借錢的事情。國學派似乎承認自己目前有些窘迫,需要一些文化和學術上的借貸,心里大概想以后成了氣候,要把借來的東西都還回去。也許我們有朝一日可以以中國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化,和西方劃清界限。
可是,這有多大的可能呢?筆者沒有見過哪個國學人士,要為借來的西方學術設定償還期。看來到時候是還不起的。那么,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把不得不“借”的東西“要”過來,變成自己的財產呢?
這就是筆者對國學要說的幾句最關鍵的話:中國正在走向世界。中國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會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把西方的傳統當成一種人類的傳統,當成我們自己的傳統,“要”過來就完了。比如希臘羅馬的古典學術,不僅是希臘人、意大利人學,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都在學。后面的這些“外國人”學起來,從來不說他們要“借鑒”希臘羅馬的傳統云云。人家就是把這些古典傳統當作自己的文化精神。整個西方世界都能受文藝復興、啟蒙主義之益,也正在于此。
所謂“借鑒”,實際上還是體現了國學派對融入世界文化的不甘心,要用個“借”字表示內外有別。一些自稱是文化保守主義的知識人,明明同時受了西方和中國文化的影響,卻也要挖空心思表明這些影響屬于“借貸”之列,而中國文化才是自己的根本。帶著這種傳統弘揚國學,筆者怕是“國學院”會變成一塊文化上的“自然保護區”,與現實的世界越來越不搭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