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列文森是少見的有形而上學素質的西方漢學家,外加隨身的猶太文化背景,其見識因此格外不同凡響。在其被譽為 " 天才 " 之作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列文森將清末民初的大儒廖平( 1852 - 1932 )看作儒學 " 已經失去了偉大意義 " 的 " 一個無足輕重的例子 " ,一生 " 一事無成 " ,著作充滿了儒家傳統 " 令人厭惡 " 的 " 空言 " ,其歷史意義僅在于代表儒學宣告了退出 " 歷史舞臺 " 。列文森還說,廖平思想 " 稀奇古怪 " ,恰恰證明他的生活太 " 平庸 " ,沒有與現實政治保持生機勃勃的聯系;就算康有為抄襲了廖平,仍然比廖平了不起,因為康有為將廖平的抑古尊今思想轉變成了現實的政治改革行動,為儒學提供了 " 最后一次服務于近代中國政治的機會 " :廖平 " 度過了平庸的一生 " ,而康有為卻 " 差點因吸收了廖平的觀點而喪生 " 。
按照這位有如此 " 形而上學素質 " 的思想史家評價某種形而上學是否了不起的尺度,羅森茨威格、拜克、索勒姆、列維納斯等現、當代猶太教思想大師都 " 平庸一生 " ,其歷史意義不過在于他們代表猶太教思想徹底退出了 " 歷史舞臺 " ,因為他們的思想同樣沒有轉變成任何現實的政治改革行動。至于本雅明那樣的猶太 " 形而上學 " 家竟然畏懼現實政治到了甘脆自己了斷的地步,其思想當然就更是 " 稀奇古怪 " 的 " 空言 " 無疑了。海德格爾參與了十個月的納粹政治,按理說,與康子的 " 維新 " 沒有什么實質差別,其形而上學是否因此才非 " 空言 " 呢?但這位二十世紀公認的泰西頭號形而上學家說,要求形而上學為革命作準備,實在滑天下之大稽,就像說 " 木工刨床不能載人上天,所以應當丟棄它 " (《形而上學導論》)。列文森的所謂 " 天才 " 之作不過膚淺的雜感隨筆而已,人說其有什么了不起的洞見,實屬一派謠言。
列文森以 " 現實歷史效用 " 妄說廖平純屬凡夫談圣人,自絕于士林,但對自上朝到國朝的經史家們的評斷,就不能這么說了,諸論無不有點古文家的 " 家法 " :訓詁、明物考辨到家,就是絕活,否則就是 " 恢怪 " 之論。于是,經史家們盛贊廖子平分今古,《今古學考》為 " 不刊之作 " (俞樾)、 " 貫徹漢師經例 …… 魏晉以來未之有也 " (劉師培)。到國朝學界,這 " 家法 " 大為擴充:什么 " 科學性 " 、 " 歷史潮流 " 、 " 合符理性 " 。在這些現代的新古文家 " 家法 " 看來,廖子二變以來的論著,都是沒有 " 科學性 " 的妄言,必然為 " 歷史潮流 " 淘汰。
如此 " 家法 " 與廖子的形而上學有何相干?泰西的 " 科學性 " 、 " 歷史潮流 " 、 " 實證理性 " 比我華夏王土厲害不知幾何,未見把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判死,怎么就可以判死廖子的天學?
幸好廖子精通干嘉功夫,不然考據家總會有把柄,必譏其不通絕活還自標高超。廖子了不起,他用干嘉功夫做出絕活后,馬上將這絕活判為生盲: " 國朝經學,喜言聲音訓詁,增華踵事,門戶一新,固非宋明所及。然微言大義,猶嘗未聞,嘉道諸君,雖云通博,觀其共撰述,多近骨董,喜新好僻,凌割《六經》,寸度銖量,自矜淵博,其實門內之觀,固猶未啟也。 " (《經話》甲編卷一 4 )六經中有微言大義,這不是訓詁、明物考辨到家就可以得到的, " 知圣 " 才是搞通六經的真正起點。
為什么事經學要 " 知圣 " ?哲學是圣人之事,經學乃哲學,因此要 " 知圣 " 。廖子了不起,他敢踏謔(我巴人方言)以史學取代或冒充哲學:以經為史者, " 以蛙見說孔圣,猶戴天不知天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 " 。自近代科學興盛以來,歷史科學和歷史意識 " 還經為史 " 在西方同樣氣勢洶涌,有西式干嘉功夫(古典語文學)的尼采敢于詆毀歷史科學,捍衛哲學: " 即便真正心地善良地行使歷史的公正,也是一種可怕的德性,因為它總是損害生者,使之衰亡,歷史的判決永遠是一種毀滅。 " (《歷史對人生的利弊》 7 )尼采為了哲學可以詆毀歷史科學,廖子為什么就不可以詆毀古文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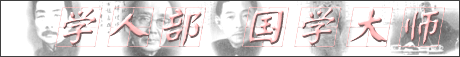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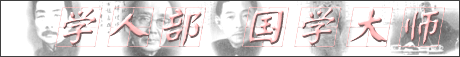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