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嚴復,就不能不說到北京大學。嚴復和這所名校可謂有著不解之緣。其因緣關系,可溯至大學的初創年代。京師大學堂成立于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是光緒皇帝“廢八股、興西學”的重要舉措之一。而在此一年前,嚴復出于對維新新政事業的熱心,大力協助友人張元濟在京師設立通藝學堂,不僅為學堂命名,還積極為學堂引薦師資,他的侄兒嚴若潛是該學堂的常駐教員,他自己也在學堂作“西學門徑功用”的專題講座。百日維新失敗后,張元濟被革職離京,通藝學堂被并入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1902年,應當時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張百熙之邀,嚴復出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1912年,嚴復被正式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接管大學堂事務。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嚴復自然而然就成為北京大學歷史上第一位校長。雖然嚴復真正掌管北大的時間很短,僅8個月之久,但在北大的百年史中,這幾個月的意義卻事關生死存亡甚為關鍵,嚴復為北大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嚴復剛接手京師大學堂時,正處在清政府統治危機的浪尖上:校舍先被義和團改為神壇,后為八國聯軍占領,學校關閉,師生流離,圖書儀器蕩然無存,存款僅有萬金,處境艱難,大學堂名存實癱。嚴復曾在家書中說:“大學堂每月至省須二萬金,即不開學,亦須萬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學部一文不給,豈能為無米之炊?”無奈此時民國政府新立,國庫一貧如洗,嚴復盡所能自籌,從華俄道勝銀行,借得7萬兩款項。
可是這7萬兩僅僅是杯水車薪。當時的中國,正處于袁世凱獨裁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袁世凱加緊搜刮民脂民膏,縮減其他部委經費,全力支持其軍隊建設,擴大其親信部隊的力量,以此來鞏固他并不牢靠的統治基礎。因此,教育經費成了第一個犧牲品。1912年6月,財務部發布通令,宣布京外各衙門及學校職教員月薪在六十以下者,一律照舊支付,而在六十元上者,一律暫支六十元。這一通令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北京大學已有數月領不到經費,辦學情況岌岌可危。
除去缺少辦學經費外,由于民國初期的政治派別斗爭異常紛亂,接著便是有人在報紙上造謠攻擊,再加各種運動差事,嚴復感到難以自全,“極難對付”。他一方面采取了歸并科目,精簡機構等措施來縮減開支,并通過再次借款,來保證日常的教學工作,另一方面,他上書議會,反對財務部為了解決財政危機而緊縮辦學經費。他提議,“為今之際,除校長一人準月支六十元,以示服從命令外,其余職教各員,在事一日,應準照額全支。”
孰料,7月7日,教育部下達結束北京大學的命令,稱“大學校自開辦至清末,凡歷十余載。中間更經喪亂,因陋敷陳”,“學生之班次雖增,陶植之成績未著”,“政體既變,各方對大學咸有不滿之意”。同時,教育部還頒行“北京大學結束辦法”(九條),決定學生提前畢業,不授予學位,一律不招新生。
教育事關國運,不可不辦。在英國留學的數年,嚴復已經認識到,歐洲堅船利炮背后,是一整套完善的社會制度,正是這樣的一種社會契約,保護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以及社會其他各項事業,使之有利于促進社會改革。而教育,正是為了服務于社會,為了傳遞有效信息,為了提高整個社會生產力,為了創造出一種生機勃勃的更為先進的社會文化。
嚴復寫下《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說帖》直呈當局并向社會吁請支持北京大學辦學。他認為:北京大學自創辦以來,集中了當時的最好人才與最大物力,經過十年的艱苦經營,才獲得了全國最高學府的地位。“一旦輕心調之,前此所糜百萬帑金,悉同虛擲,十分可惜”,辦大學既為造就人才,也為“保存一切高尚之學術,以崇國家之文化”。至于辦學程度的問題,世界上文明國家各有著名大學十幾所,乃至幾十所,我國僅此一所尚不克保存,豈不令人痛心!而北大設立的各種學科,“是則為吾國保存新舊諸學者起見”,“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無學者”。與此同時,嚴復還寫了《分科大學改良辦法說帖》呈給教育部,詳細闡明創辦新式北京大學的指導思想與改革措施,提出“兼收并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的辦學思想,要使北京大學成為“一國學業之中心點”。
嚴復為尋求北大生存與發展所作努力,得到社會各界和廣大師生的同情與支持。北大文、法、工、農四科的學生代表,聯名提出說帖或請愿書,抗議停辦北京大學,支持嚴復意見,有的甚至提出北大脫離教育部自行辦學的意見。在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下,7月10日,由蔡元培主持“全國臨時教育會”撤銷了擬將北京大學停辦的原決議,并參照嚴復的意見,提出九條解決辦法。為了解決財政的困窘局面,嚴復又一次為籌款奔波,終于從華北銀行借得20萬兩銀子,使北大再次渡過難關。由于嚴復的學問和聲望在海內外有相當影響,同年7月29日,英國教育會議宣布承認北京大學及其附設的譯學館均為大學;倫敦大學也宣布承認北京大學的學歷。北大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由此奠定。
在嚴復的主持和領導下,北大的辦學和改革一時頗有起色。然而,因為派系斗爭等種種原因,嚴復于1912年10月,被迫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離開了北京。在同年11月嚴復為預科學生所撰寫的《大學預科<同學錄>序》中,似乎可以看出嚴復當時的無奈心情:“天下之理,非年時之學所能盡;一國之事,非一哄之眾可得專也,敬告吾黨慎之而已。”
從北京大學卸任后的嚴復,漸漸淡出了中國的教育舞臺,轉向了政治舞臺。民國三年(1914年),他任袁世凱政府參政院參政、總統府外交顧問。似乎與中國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為、林紓等一樣,嚴復晚年的思想趨于保守,從資產階級改良派變成保守派。而他遺言的第一條也強調了這一點: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但是他的愛國之情和憂患意識始終未變。1916年嚴復寫給好友熊純如的信中提及了這種感情:此番英使朱爾典返國,仆往送之,與為半日晤談,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朱見慰曰:“嚴君,中國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于無效,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復聞其言,稍為破涕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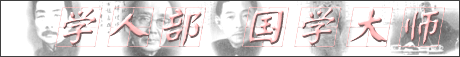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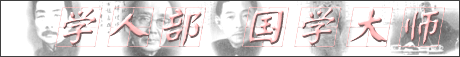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