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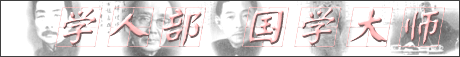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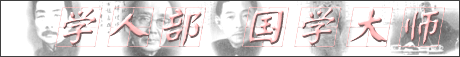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
|
|
|
||
|
|
大師生平|著作年表|著述索引|作品選讀|大師研究|研究著述|書品推介|研究學人|相關鏈接
|
|
|
要不要“回到傅斯年”? ——“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斗爭”的再解讀
|
|||||||||||||||||||||
|---|---|---|---|---|---|---|---|---|---|---|---|---|---|---|---|---|---|---|---|---|---|---|
黃 波 |
||||||||||||||||||||||
謝泳先生寫過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到傅斯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沒有安排好的道路》一書。何謂“回到傅斯年”?就是回到傅斯年的史學觀。而傅斯年的史學觀,按謝泳的概括,“簡單說就是‘史學即是史料學',他認為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只 所謂“史學即是史料學”,這其實不是什么創見,中國的舊史學向來如此,西方也有蘭克及其影響下的蘭克學派。蘭克的治史名言即是史學的“目的僅僅在于展現歷史的真情”,“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可是現在為什么謝泳要鄭重其事地提出一個“回到傅斯年”的命題?這其中蘊含著怎樣的意義?原來,曾幾何時,史學是不是史料學的問題已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關乎學者態度、立場、階級屬性,關乎“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斗爭”的重大問題。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歷史學界,有所謂“兩條道路的斗爭”,即自稱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唯物史觀派對史料學派的斗爭。這場斗爭以1958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的一篇題為《厚今薄古,邊干邊學》的報告揭幕。陳在講話中說:“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幾十年來究竟有多大的貢獻呢?他們積累了些資料,熟悉了些資料,據說就很有學問了,有多大的問題,有多大的貢獻。積累資料如果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領導,那么他們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則有什么用呢?”以此為基調,中山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等高等學府的歷史系學生分別發起了對陳寅恪、岑仲勉、童書業、徐仲舒等著名學者的批判,這種批判一直追溯到1949年以前歷史學界的“三大老板”——胡適、顧頡剛、傅斯年。批判的武器和批判的內容從山東大學歷史系學生所作的一首打油詩中可見端倪: 厚古又薄今,理論看得輕; 馬恩列斯毛,從來不問津。 報刊和雜志,當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筆大資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稱二陳; 史觀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論有啥用,史料功夫深。 意思很清楚,可惜詩不太雅正。與此相比,還是學者的分析有分量些。且看唯物史觀派領軍人物范文瀾和胡繩的文章。范文瀾的《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見中國社科版《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發表在陳伯達的報告傳達之后,要點有三:厚今薄古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厚古薄今是資產階級的學風;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線的斗爭。范氏在文章中指稱,以胡適為代表的史學家大搞煩瑣考證就是“企圖使學術脫離革命的政治,變成沒有靈魂的死東西”。胡繩題為《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的長文(收入人民版《棗下論叢》)發表在1956年,語氣較為平和,其中重點批判了傅斯年的歷史觀,他說:“用史料學代替歷史學,既破壞了歷史科學,也會把史料學工作引導到錯誤的路上去。無論是史料的‘內部'的考證還是‘外部'的考證,目的都應當是提供對歷史的科學認識的可靠基礎;如果脫離整個史學的科學研究而孤立地進行,就會迷失方向,無目的地沉溺在歷史的海洋中。”無論是學生還是學者,對史料學派的不滿都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史料學派是只講求占有資料、考訂史實,拒絕理論(當然應是唯物史觀)的指導,因此無法深入歷史現象的本質以發現各種現象之間的聯系及其客觀規律。 回顧這場“斗爭”,現在可以說范文瀾等人對史料學派的指責沒有什么根據,因為史料學派中人并非一定排斥理論,如顧頡剛早在1940年為《史學季刊》作《發刊詞》時就針對考據與史觀之關系說過如下的意見:“歷史科學家慣于研索小問題,不敢向大處著眼……若不參與歷史哲學,俾作相當之選擇,而輒糜費窮年累月之功夫于無足輕重之史實中,真固真矣,非浪擲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歷史哲學指導之歷史科學,皆無歸宿者也。”試看顧氏此論與上引胡繩的話有何區別?顧頡剛另有一句名言,見于他為《古史辨》第四冊所作的序言:“唯物史觀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內都滲入些”,這句話在五十年代曾頗讓顧的批判者憤怒,其實顧氏“味之素”云云何嘗不是從另一角度肯定唯物史觀的功用? 本來按照正常的邏輯,史料派與唯物史觀派之間不應該發展到無法并立的地步,不僅是顧頡剛等人分明有贊同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的話,而且就是范文瀾、胡繩不也曾對史料學家的勞作表示過肯定?胡繩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明白無誤地說:“許多中國的史學家們繼承了清朝‘漢學家'們的工作,而且利用了從現代歐美傳來的各種科學知識和比較精密的邏輯觀念,而在史料考訂上,取得了不少成績。他們的這種工作,現在看來,并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們的工作成績和工作經驗不應當被抹煞而應當加以接受,加以發揚。”盡管如此,“路線斗爭”云云還是向我們這些后世讀者提示著過去那場爭論的嚴重性,否則當年執教中山大學的陳寅恪也不會憤怒地拒絕為學生開課了。那么兩派史學家分歧的實質在哪里呢?首先是誤讀的存在,正如謝泳所分析:“對史料學派的批判是構造了一個史料學派沒有理論的假設,在這個前提下,以所謂史料與理論的輕重和求真與致用的矛盾為相互對立的假設,對前者進行了否定,其實這些問題都是不存在的。因為史學常識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沒有理論的史料,也根本沒有過史料的理論”;其次我以為應該是對“理論”“史觀”內涵理解的歧異,如前所引,唯物史觀派固極重理論的引導,史料學派也并未排斥,但史料學派反對將“理論”庸俗化,坐實為唯物史觀,像顧頡剛就認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跡,書籍真偽,需用于唯物史觀的甚少。”而所謂唯物史觀派始終堅持歷史研究應在以現實政治為最高導向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同一“理論”,大異其趣,所以范文瀾才會號召要對“堅持學術獨立”“拒絕學術為政治服務”的“胡適門徒”開戰。最后,我們還可以認為,在歷史研究的終極目的是什么的問題上,雙方也是各有主張。“歷史有什么用?”當年法國年鑒學派的大師布洛赫曾被稚子的這句質問震撼,大概所有埋首故紙堆的人都無法回避這一問題。“用”的含義豐富,如果僅僅定義為實用意義上的“用途”,史料學派中人的態度是:歷史學可以有“用”,但歷史學家不應去求“用”,像顧頡剛就堅定地認為:“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結果,而不是作學問的目的”。而唯物史觀派中人則認為,歷史學必須有“用”,歷史學家應該去主動求“用”。胡繩特別舉了個例子來批判傅斯年,因傅氏在1932年寫了篇《明成祖生母紀疑》而且引發學界的熱烈討論,胡繩乃對此問道:“誰是明成祖的生母,這問題有什么意義,這是傅斯年自己也說不出來的”。現在看來,明成祖的生母是誰的確是個瑣屑的問題,但是否就真無意義還大有可商處,試想一下,如果與此相關的小問題都弄明白了,人們對明宮廷乃至明朝政治的了解會不會更深一些呢? 通過對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之爭的回顧,走過一段彎路的我們終于明白,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熟悉、考訂史料都是第一位的、基礎性的工作。所以謝泳先生提出了當代中國史學要回到傅斯年的傳統的觀點。這一觀點是對過去那段迷誤的反正,有合理性,可是對比西方史學的發展,我們似乎又不能如此自信。西方在蘭克學派以后,有所謂批判的歷史哲學有年鑒學派,有斯賓格勒有湯因比有布羅代爾等大師,無不是對以實證史學為特色的蘭克學派的揚棄。如果史學研究的惟一正途就是傅斯年的傳統,大概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也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也罷,都不是什么有價值的著作,這豈非荒唐?另外,中國人的實用理性向來發達,中國人思維、治學的特點本來就“不玄想,貴領悟,輕邏輯,重經驗”,所以歷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雖然重要,但難道我們不應同時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國抽象思辨那種驚人的深刻力量?俄羅斯知識分子有言:“我的心因為人類的苦難而受傷”,一個歷史的研究者是否也應具備這種世界眼光和人類意識?還有一點,強調“回到傅斯年”似乎還忽略了學者稟賦、氣質之差異,其實,只要沒有現實政治的干擾,何妨讓幾個沒有興趣鉆史料的人去放言高論?不著邊際之處,不妨一笑了之,然而有時也許還會有靈光一現呢。比如八十年代那些轟動一時的名著當下屢被人譏為“空疏”,可是只要一堆“空疏之論”中有片言只語啟發你深沉思考,這不就夠了嗎? 來源:光明書評
|
 |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