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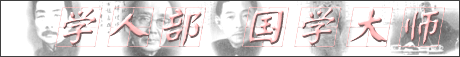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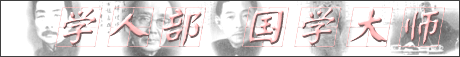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
|
|
|
||
|
|
大師生平|著作年表|著述索引|作品選讀|大師研究|研究著述|書品推介|研究學(xué)人|相關(guān)鏈接
|
|
|
|
傅斯年眼中的中國通史
|
|
|---|---|---|
新華網(wǎng)
□羅厚立
|
||
20世紀(jì)初年成長起來的中國學(xué)者中,影響大而真正識見高的并不多,傅斯年應(yīng)屬其一;但他在史學(xué)言說中卻是相對“失語”者,尤其是在中國大陸。近年王?森關(guān)于傅斯年的專書出版,重建其學(xué)術(shù)、思想及其政治活動,傅氏的形象可謂面目一新。可惜此書是英文,大陸稍差的圖書館或不藏,能讀到者似不多。以傅斯年的著述和學(xué)術(shù)功業(yè),其影響應(yīng)比現(xiàn)在大許多;但由于政治等原因,傅氏作品在大陸長期少見,僅近年稍有選本,實妨礙其思想、學(xué)術(shù)之流傳。今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傅斯年全集》,雖仍不夠全,并略有訛誤,到底提供了研究傅斯年的基本資料。 蔣廷黻曾經(jīng)回憶說,傅斯年論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jīng)驗”。的確,言有所本而眼光通達,是傅氏言論的一大特色。但在具體研究中,他似更重視史事的橫向關(guān)聯(lián),多次強調(diào)史事與周圍的聯(lián)系超過其與既往的聯(lián)系。傅先生以為,“古代方術(shù)家與他們同時的事物關(guān)系,未必不比他們和宋儒的關(guān)系更密;轉(zhuǎn)來說,宋儒和他們同時事物之關(guān)系,未必不比他們和古代儒家之關(guān)系更密”。法國史家布洛赫后來也曾引阿拉伯諺語“人之像其時代,勝于像其父親”,以說明理解任何歷史現(xiàn)象都不能脫離其發(fā)生的特定時代。 故傅斯年主張:敘述史事應(yīng)“一面不使之與當(dāng)時的別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與別一時期之同一史合”。這與側(cè)重專題研究的陳垣看法相近,而與提倡治“通史”的錢穆頗有距離。陳垣曾告訴蔡尚思,“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頗空泛而弘廓,不成一專門學(xué)問”;只有“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錢穆則主張歷史是整體的,治史要“通”,而不甚贊成以“事件”為中心的專題研究,以為“事件”一旦抽出,則可能切斷其縱橫關(guān)系,反“無當(dāng)于歷史全體之真過程”。在其記憶中,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歷史系的傅斯年主張“先治斷代史,不主張講通史”,兩人為此頗有些沖突。 那么,是否傅斯年在非史學(xué)領(lǐng)域才體現(xiàn)其語語四千年的通達風(fēng)格呢?其實不然,傅氏早年在北大讀書時便主張歷史可“斷世”而不必“斷代”,且已形成其新穎而明晰的“斷世”體系。一般皆知陳寅恪治史有其一以貫之的核心觀念,即“種族與文化”,其實傅斯年亦然。他在五四前所著的《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已明確提出:“研究一國歷史,不得不先辨其種族。誠以歷史一物,不過種族與土地相乘之積。種族有其種族性,或曰種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種族一經(jīng)變化,歷史必頓然改觀。”故其中國史之“斷世”,即“取漢族之變化升降以為分期之標(biāo)準(zhǔn)”。 而傅斯年的“種族”概念,其實也更多是“文化”的。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所謂‘諸夏’、‘漢族’者,雖自黃、唐以來,立名無異;而其間外族混入之跡,無代不有。隋亡陳興之間,尤為升降之樞紐。自漢迄唐,非由一系。漢代之中國,與唐代之中國,萬不可謂同出一族,更不可謂同一之中國。”故他斷言:“自陳以上,為‘第一中國’,純粹漢族之中國也;自隋至宋亡,為‘第二中國’,漢族為胡人所挾,變其精神,別成統(tǒng)系,不蒙前代者也。”在同一“土地”之上,先后兩個“中國”的差異不僅體現(xiàn)在后者皇室將相多非漢種,更主要的是“風(fēng)俗政教”的大不同。 北伐后傅斯年成為北大教授,上課時仍貫徹這一早年確立的分期觀念,其印發(fā)的《中國通史綱要》,再次明確“以‘民族遷動’為中國史分期之標(biāo)準(zhǔn)”,而具體的分期也基本相同。他在1931年給陳寅恪的信中重申:“中國之國體,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漢承秦緒、唐完隋業(yè),宋又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兩代,雖民族不同,其政體則皆是元代之遺耳。”當(dāng)然,傅斯年也注意到歷代“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別作‘枝分’”;其枝分的標(biāo)準(zhǔn)分別是:上世為“政治變遷”,中世為“風(fēng)俗改易”,近世為“種族代替”。 在“中世”一段,“自爾朱亂魏,梁武諸子兄弟鬩墻、外不御侮之后,南北之土客合成社會,頓然瓦解;于是新起之統(tǒng)治者,如高齊、如宇文周、如楊隋、如李唐,乃至侯景,皆是武川渤海族類之一流,塞上雜胡,冒為漢姓,以異族之個人,入文化之方域。此一時代皆此等人鬧,當(dāng)有其時勢的原因,亦當(dāng)為南北各民族皆失其獨立的政治結(jié)合力之表現(xiàn)。”正因南北朝各族“皆失其獨立的政治結(jié)合力”,所以才有隋唐“民族文化之大混合”。故“唐代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為中國社會階級之大轉(zhuǎn)變”。 他早年論證隋、唐皆“外國”說:“君主者,往昔國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虜,其不純?yōu)闈h族甚明”。而“唐之先公,曾姓大野”。不論是原姓李氏而賜姓大野,還是原姓大野而冒認(rèn)李姓,皆當(dāng)疑而證之。更廣泛地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偽齊陳,直認(rèn)索虜為父,不復(fù)知南朝之為中國”。當(dāng)時將相,“鮮卑姓至多,自負出于中國甲族之上;而皇室與當(dāng)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華人”。若一般民俗,則“琵琶鮮卑語、胡食胡服,流行士庶間”,載記可考者甚繁。可知“隋唐所謂中華,上承拓拔宇文之遺,與周漢魏晉,不為一貫。不僅其皇室異也,風(fēng)俗政教,固大殊矣”。 后來陳寅恪申論李唐帝室非漢姓,曾引起軒然大波,朱希祖嘗力辯其非,蓋認(rèn)為此說或暗示中國人久已無建國能力,當(dāng)日本侵華之時而言此,太不合時宜。早存此見的傅先生聞此則“倘佯通衢,為之大快”。其實陳先生所見者遠,在他看來,必知“李唐先世疑出邊荒雜類”而“非華夏世家”,而后李唐三百年“政治社會制度風(fēng)氣變遷興革所以然之故,始可得而推論”。故“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長,遂能別創(chuàng)空前之世局”。 或即在此種族文化融合意義之上,傅斯年看出陳先生所發(fā)現(xiàn)者乃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事件,反映了時代的結(jié)構(gòu)性劇變,即其所謂“時代之Gestalt”。他申論說:魏晉以來“政治之最大事”即“整齊豪強之兼并,調(diào)劑中正官之大弊”。然“南朝立國本由過江之名士,濟以吳會之舊門,為社會政治支配之主力,故此局面打不破”。北朝“以沿邊之雜胡,參之中原之遺族而成之社會”,其政體雖與南朝略同,社會成分畢竟有差異。統(tǒng)一之后,“南北門閥各不相下,而新舊又異其趨向”,其終能形成以諸科考試代九品中正的制度,“與隋唐帝室出身雜胡不無關(guān)系”。此后科舉制影響中國社會千余年,誠為“中國社會階級之大轉(zhuǎn)變”。 傅先生斷定,“此事關(guān)系極大,此一發(fā)明,就其所推類可及之范圍言,恐不僅是中國史上一大貢獻而已”。從唐代帝室種族考證“推類”至影響中國社會千余年的科舉制,非胸中素存四千年史事的大手筆不易見及。魯迅曾說,“凡人之心,無不有詩”。一讀他人之詩而“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蓋心中先有詩,則詩人“握撥一彈,心弦立應(yīng)”。大約總要識力見解相近,然后可產(chǎn)生撥輒立應(yīng)的共鳴。傅先生能看出陳先生之所欲言及其可能推廣的影響,誠可謂知音。 而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卻常被誤解,其“史學(xué)即史料學(xué)”的說法更曾引起廣泛爭議。傅先生明言“反對疏通”,主張以“存而不補”的態(tài)度對待材料,以“證而不疏”的手段處置材料,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但其自身作品,特別是其著名的《夷夏東西說》和《性命古訓(xùn)辨證》,又何嘗少了“疏通”!他相當(dāng)贊賞清儒“以語言學(xué)的觀點解決思想史問題”的方法,更主張“思想非靜止之物”,故在“語學(xué)的觀點之外”,更須“有歷史的觀點”,以疏通特定觀念“歷來之變”。不過,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于“妄誕”,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吧。 其實傅斯年不僅歷史眼光通達,他觀察時事同樣敏銳。早在1918年6月,他就不僅看出新俄之“兼并世界,將不在土地國權(quán),而在思想”;更預(yù)見到“將來西伯利亞一帶,必多生若干共和國”。當(dāng)時恐怕極少人能有這樣的未卜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說,“吾輩批評時事,猶之批評史事,豈容局于一時耶”。正因其觀察眼光不局于一時,復(fù)有其一貫的種族文化視角,故能所見深遠。《全集》中類此睿見比比皆是,實在值得認(rèn)真研讀;其書信、遺稿中還有不少論學(xué)論時之作,惜未收入。 《傅斯年全集》,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