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曾經是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當他倡導維新運動、領導戊戌變法時,他代表和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為推動社會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復辟帝制運動同流合污時,他就站到了歷史進步的對立面,成為社會前進的阻力。
在民國初年,康有為熱心于尊孔復古,并有一系列表現。史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康有為熱心于尊孔復古是為了反擊北洋軍閥橫行中國的黑暗統治,指斥袁記中華民國,因此其言行尚不失某種歷史的進步性。不難看出,這種觀點對于袁世凱掀起尊孔復古的思想逆流和推行帝制復辟的倒行逆施是持否定態度的,但對康有為熱心于尊孔復古的行為則多所肯定。持這種觀點的人還認為,康有為支持尊孔復古是為了用中國舊有的文化對抗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用中國已有的文化謀中國文化的新出路;康有為批判袁記中華民國,實際上是同情孫中山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事實是否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康有為支持尊孔復古不僅不是用中國舊有的文化對抗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也不是用中國舊有的文化謀中國文化的新出路,而是用舊文化對抗新文化,為帝制復辟運動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
一般來說,隨著政權的交替,制度上的立新較之思想上的去舊要容易得多。民國成立后,資產階級文化政策、教育體制逐漸確立,新的文化方針、教育方針也逐漸得到貫徹,但守舊勢力如舊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紳、舊學名流、前清遺老以及新舊軍閥仍頑強地堅守自己的陣地,維護他們久所尊奉的傳統文化,對新教育極端仇視。他們將力量集結起來,瘋狂地反撲新文化、新教育。而康有為就是其中的重量級人物。康有為對于民國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先是表露出極大的失望與悲憤,繼而向教育部表示抗議,并予質問,觀點鮮明,口氣冷峻。康有為說:“今吾國生民涂炭,國勢搶攘,道揆凌夷,法守掃蕩,廉恥靡盡,教化榛蕪,名為共和,而實共爭共亂,日稱博愛,而益事殘賊虐殺,口唱平等,而貴族之階級暗增,高談自由,而小民之壓困日甚,不過與多數暴民以恣睢放蕩,破法律,棄禮教而已。……頃乃聞部令行飭各直省州縣,令將孔廟學田充公,以充小學校經費,有斯異政,舉國惶駭,既已廢孔,小學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長成,未知猶得為中國人否也?擬將為洪水猛獸也?嗚呼哀哉!”(康有為:《復教育部書》)如果這僅僅是康有為個人的哀鳴,倒也不足為奇。事實是,在民國初年的尊孔復古活動中,康有為急不可待地以精神領袖面目登臺。有了康有為的再三鼓噪,孔教會在陳煥章的策劃下,又是“請愿”,又是“上書”,鬧得泥動水響。在孔教會的聯絡、呼吁下,政界要員如黎元洪、馮國璋等人也積極響應。在尊孔守舊、反對新式教育的一片唱和聲中,孔教會、孔道會、孔社、孔子祭奠會、尚賢堂、國教維持會、全國公民尊孔聯合會、四存學會等一些保守的文化社團組織紛紛出籠,隨之興起的尊孔活動便是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誕辰紀念會等。思想界的尊孔回流與守舊派發動的尊孔活動,為袁世凱復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礎與社會基礎。
袁世凱當時一意復辟帝制,數次致電康有為,請他進京主持名教。一個要提倡名教,一個要復辟帝制,于是,他們很快走到一起來。日后的歲月證明,康有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復古,并不是要為中國文化謀新路,也不是對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不滿,而是意欲恢復大清王朝。有些論者依據康有為在民國元年12月22日所作的《〈不忍〉雜志序》中提出的“十不忍”,認為他反對袁記中華民國這個政治實體、“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為”,同情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真是這樣嗎?答案也是否定的。這一說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不值一辯。無論從什么角度看,康有為呼應袁世凱復辟帝制,在理論上推波助瀾,毫無疑問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點。我們沒有必要為賢者諱。
認真推究起來,康有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誤,既有個人主觀因素的作用,也有時代條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為只反對所謂“袁記中華民國”而擁護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的問題。戊戌變法以后,康有為的思想并沒有隨著歷史進步的步履而前進。辛亥革命之前,他作為保皇黨領袖以《新民叢報》為陣地,向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難并予以惡毒攻擊。辛亥革命發生時,他又滿懷不安,“惴惴恐懼”。辛亥革命一個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歡呼革命的勝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場上哀嘆“亡國”。可見,他對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始終就沒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擁護之情?
其次,辛亥革命后,康有為以“亡國臣民”自居,對新生的中華民國充滿敵意。辛亥年除夕前六日,康有為“感賦一首”。詩云:“絕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禪讓寫移文。玉棺未掩長陵土,版宇空歸望帝魂。三百年終王氣盡,億千界遍劫灰焚。逋臣黨錮隨朝運,袖手河山白日曛。”詩中充分流露出康有為的故國之思。緣于此,他才會有“十不忍”:“睹民生之多艱,吾不能忍也;哀國土之淪喪,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綱紀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窳敗,吾不能忍也;傷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蹂躪,吾不能忍也;睹政黨之爭亂,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失,吾不能忍也;懼國命之紛亡,吾不能忍也。”可見,他的“十不忍”表露的是他對清帝失位、朝廷被廢、孔子學說退出歷史舞臺的殘酷現實痛心疾首、悲傷欲絕的心態;他數落中華民國“十大罪狀”,根本就不是對“袁記中華民國的黑暗統治”表示抗議,而是對革命派推翻清朝強烈不滿,同時也是為復辟運動尋找借口。由此也可看出,康有為對于“袁記中華民國”掀起的尊孔復古運動有的只是惶恐之余的欣慰、失落之后的感激,根本就沒有什么不滿。
再次,正是因為康有為與袁世凱的合作,充當民國初年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才導致康有為與梁啟超這對莫逆師徒反目,分道揚鑣。梁啟超發現袁世凱在利用尊孔復古運動搞帝制復辟、妄圖再建一個封建王朝的陰謀后,幡然悔悟,毅然發起護國運動。在看到袁世凱復辟帝制運動與康有為種種助桀為虐的表演后,梁啟超不無嘲諷地說,他的老師康有為已經由一個歷史巨人蛻變為一個歷史侏儒了。
孟子說:“知人論世”。如果我們不弄清楚康有為在民國初年的政治立場及其活動,僅僅從字面上察考康氏的“十不忍”,就會得出康有為是民國初年“少有的愛國主義者”與“關心社會進步與生民疾苦的民族英雄”這樣的結論,但歷史的真情卻恰恰不然。康有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正是袁世凱迫切需要的。既然袁世凱提倡尊孔復古、策劃復辟帝制是一種逆行,那么,康有為此時醉心于尊孔復古、支持帝制復辟,也不會具有進步性和愛國精神。毒草在袁世凱身上是毒草,在康有為身上也不會變成鮮花,這是由毒草的本質所決定的。由此也使筆者不能不對評價歷史人物的理論與方法問題進行思考。毫無疑問,歷史人物是歷史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思想、行為總是緊扣時代發展的脈搏,但如何“扣”卻是因人而異、大不相同的:有的人與時俱進,始終與時代潮流同行,既是“老先進”,又是“新先進”,如孫中山、宋慶齡這樣的杰出人物就是如此。他們永遠值得后人景仰。但有的人曾經是“老先進”,后來卻落伍了,康有為即是一例。這樣的人值得后人借鑒。我們在考察、評價歷史人物時,應該本著歷史的態度,進行客觀、科學、具體的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能簡單化。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也只有這樣,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揭示歷史的真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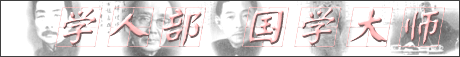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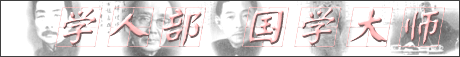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