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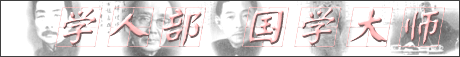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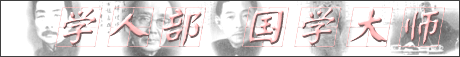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
|
|
|
||
|
|
大師生平|著作年表|著述索引|作品選讀|大師研究|研究著述|書品推介|研究學人|相關鏈接
|
|
|
|
||||||||||||||||||||||||
|
|||||||||||||||||||||||||
張艷國 |
|||||||||||||||||||||||||
書法理論典籍上,批評色彩最明顯但火氣也最大的當數項穆與康有為。項穆站在明人立場上對蘇東坡、米元章的指摘,激烈得出人意外;而康有為以晚清書法巨子的身分,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他的尚碑意識,雖說也造就了一代書風,要之終覺得大過偏激。理論的能力應該是盡量公正地評判歷史功過,因此需要周密的理性思考,只圖一時痛快,將異己者一概罵倒,這是不能令人心悅誠服的。特別是此公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名家如云的書法功績一筆抹殺,以理論家衡之未免有點滑稽。大凡一個有成就的理論家大概也很難成為創作大家。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作需要火.熱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而創作必須“偏激”。在古來,象孫過庭、蘇東坡這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的理論震聾發聵但不是理論應有的姿態,我頗疑心他并無意于做真正的理論家,而是以此為創作服務:代創作立言。因為對北碑一面倒的偏愛正是康有為書風的一大特征——當然他不取方筆殺伐之態,而是在遒勁舒展、外松內緊的摩崖書風方面浸淫良深。以如此的特殊立場視唐碑,在審美趣味上的格格不入是理所當然的。雄強的趣尚和銳意變革書風的決心,使我們想起了此公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為:“戊戌變法”的最初目的,也是希望中國從積弱中走向雄強,當然,作這樣的比附也許稍嫌牽強。但以他在政壇的一度叱咤風云而卒遭慘敗的情況看,則胸中郁勃不平之氣發為書法,該不會去傾心于容貌姣好的趙董一流,怕也是預料之中的。康有為醉心于《石門銘》,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則方圓兼備,軟筆羊毫那種特有的粗茁、渾重、厚實效果在他的線條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有異于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又不同于何紹基的單一圓勁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于線條控制帶出結構的動蕩,非四平八穩者比,亦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征之表現。但粗筆時見松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要亦一病。
|
|||||||||||||||||||||||||
轉自美術家網 |
|||||||||||||||||||||||||
| [返回首頁] | |||||||||||||||||||||||||
 |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