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讀了一則軼聞,頗為吃驚。說是抗戰(zhàn)期間,一日敵機(jī)轟炸昆明,西南聯(lián)大教授劉文典一聽到警報(bào)便往外跑,跑到中途,突然想起陳寅恪,此老視力極差,身體不好,如無人幫扶,恐怕會被日機(jī)炸爛。于是趕快折了回來,率領(lǐng)幾個(gè)學(xué)生攙扶陳寅恪往城外逃走。有學(xué)生見劉文典氣喘吁吁的,想靠近助他一把,他大聲嚷著:“別管我,保護(hù)國粹要緊!保護(hù)國粹要緊!”讓學(xué)生攙著陳寅恪先走。陳是國學(xué)大師,反對新文化運(yùn)動,蔡元培主政北大時(shí),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針,把他尊奉為一級教授。解放后,陳寅恪轉(zhuǎn)赴中山大學(xué)任教,三年困難時(shí)期,陶鑄指示要為他提供較豐富的物資供應(yīng),省、市教育系統(tǒng)的領(lǐng)導(dǎo)不大情愿,被陶鑄怒斥:“你如果眼瞎了還能像陳教授那樣寫出幾本書來,我也同樣供應(yīng)你!”——自然,這是后話。當(dāng)日逃難的時(shí)候還有一個(gè)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這時(shí),只見沈從文也在人流中跟了上來,劉文典轉(zhuǎn)身罵道:“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xué)生跑是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干嗎要跑呀!你干嗎要跑呀!”劉文典這一罵可真太出格了。別說沈從文也是自己的同仁,也別說沈從文已是名滿天下的小說家,就算是一個(gè)湘西來的渾小子,也絕不可以讓敵寇之刀去殘害。原來,劉文典一直看不起搞新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人。一次,在西南聯(lián)大的教務(wù)會議上,他就嚷嚷:“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可我不會給沈從文4毛錢。沈從文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如果把這則軼聞作為笑話,它可載入古今笑話大全了;如果把這則軼聞作為文化精英的雅事,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劣根性就非常典型了。事實(shí)上,門戶之爭、黨同伐異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一大負(fù)面,并深刻影響了整個(gè)社會生活。放在意識形態(tài)上,就是不允許“異端邪說”的存在;放在政治層面上,就是不允許對立面另樹一幟;放在日常的人際關(guān)系上,就是等級的森嚴(yán)和彼此妒忌。故此,外行與內(nèi)行之間,內(nèi)行與內(nèi)行之間,很難在一個(gè)和諧的氛圍里,開誠布公、推心置腹、心平氣和地討論一個(gè)問題,操辦同一件事。回首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yùn)動,從詩歌到小說,從治史到治文,種種的不足和遺憾,都緣于缺乏當(dāng)年對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及創(chuàng)新。傳統(tǒng)國學(xué)的衰敗,也是因?yàn)槲茨芘c時(shí)俱進(jìn),從時(shí)代新潮流中不斷注入新的觀點(diǎn)和方法,材料及識見。國學(xué)大師和新學(xué)健將也只能各說各話,互相攻訐,無助于共同熔鑄出一個(gè)領(lǐng)時(shí)代風(fēng)騷的中華先進(jìn)文化。
孔夫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大方向基本一致就可以了,做官和做事都容許有不同的形態(tài),不同的方式。穿衣吃飯各取所好,讀書經(jīng)商各憑愛好,性格不同處事各異,只要我們承認(rèn)這是常識,就很容易以常理去營造一種和諧的氛圍,讓種種勾心斗角的兵法遠(yuǎn)離社會,從而使人際之間洋溢著公平正義,流貫著誠信友愛,寬容、退讓、諒解、支持成為我們社會司空見慣的天然行為。
來源: 防城港日報(bào)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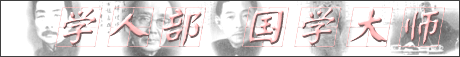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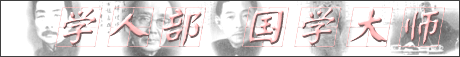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