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學吳小如先生的一篇短文《記兩位老師的談話》中,回憶林庚先生(字靜希)的一段談話:"同靜希師談話是從當前師資青黃不接的情況開頭的。靜老慨嘆道:‘當年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教我的老師劉文典,陳寅恪這些大師,都沒有文憑。'"林庚先生的話點出兩點:其一,劉文典是學術大師,其二,劉文典是沒有文憑的學術大師。這樣的大師我最欣賞,因為真正的學術并不寫在文憑上,而真正的大師往往不屑于文憑的有無。這樣的大師決不希求用文憑來證明自己,他們通常用自己來證明自己。
劉文典幼年入讀教會學校,奠定了良好的英文基礎,以后擔任《民立報》翻譯,《新青年》英文編輯,蓋伏筆于此。十七歲入安徽公學,受教于陳獨秀,劉師培,國學根底培植更深,而熏陶感染,思想革命激進,博涉廣獵。二十歲東渡日本,留學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同時師從章太炎學《說文》,與魯迅同為及門弟子,中西之學,無不探求。灰心政治以后,轉而治學,執教北大,一面教書,一面從事古籍校勘和研究,積數年之功,終有所成。一九二三年第一部專著《淮南鴻烈集解》出版,學界普為重視,提倡白話文的胡適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長編》中提到:"今年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收羅清代學者的校注最完備,為最方便適用的本子。"足見胡適對于劉文典的學力贊佩有加,所以在后來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時,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嗇地把《淮南鴻烈集解》寫入其中。
后來劉文典出版《莊子補正》10卷時,他最佩服的陳寅恪欣然為序,說:"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為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陳寅恪推許如此,可見劉文典治莊子所達之深度,無怪其挾莊子而狂放睥睨。雖然他才力雄厚,性格高傲,治學之時卻有所寬厚之處,他的《淮南鴻烈集解》,據胡適講,解釋原文,凡是與前人相合的都歸功于前人,前人錯的地方,卻"不輕斥其失",甚至因為有些宋明藏本,清代學者俞樾不易看到,而代為隱匿他的失誤,所以胡適說他"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于學者求誠之意矣。"這使人覺到很奇怪,其實正是他對于佩服的人,佩服太過,而不惜為之遮掩瑕疵。
劉文典治學嚴謹,著作豐碩,但他有一點常常為人所詬病,就是寫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從不標點,致使讀者雖知其書為好書,而難以卒讀,說他"作者不關心讀者"。不但一般讀者如此品評,胡適也說他"標點尤懶,不足為法"。但他很固執己見,有人勸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標點符號,也應該用圈點分句,使讀者容易讀通,便于理解,他卻說,既讀不通,何必讀呢?其實他大約是有意要跟陳寅恪看齊的,他最推重陳寅恪,而陳寅恪寫文章,也是用古文,也從不喜歡加標點。但也許陳寅恪學術成就更為深廣,使人高山仰止,忙于膜拜,所以就想不到去批評他了。
劉文典不但是學者,同時也是老師。他講課很有特色,所以上過他課的人都念而不忘。譬如他在西南聯大任教時,有次在課堂上對學生講,要把文章寫好,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學生紛紛不明所指,他解釋說:"‘觀'就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聽聞之后,學生們無不應聲叫好。
但他上課也有不妙的地方,因為他嗜吸鴉片,有時候上課煙癮來了無法過癮便狂抽香煙,由于發音多通過鼻腔,所以發音含混不清,講《文選》時,只能聽到他囁嚅而言:"這文章好!這文章妙。"因為他上課引證繁富,一堂課只能講一句,所以他 教《文選》,一個學期只能講半篇玄虛的《海賦》。
但他煙癮不來的時候,講課是很精彩的,有一則關于他的"劉文典先生三易其地講紅樓"可以約略見之。據一位曾親聆這次講座的學生回憶說,屆時早有一大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尚未黑,但見講臺上已燃起燭光(停電之故),擺著臨時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等上講臺,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里為他斟茶。劉文典從容飲盡了一盞茶,然后豁然起立,像說"道情"一樣,有板有眼地念出了他的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于是他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四個大字。 ......而他對于"蓼花汀滁"的解釋是:"元春省親游大觀園時,看到一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屬意寶釵了。......"這樣的燭光講座,真算是風趣十足,足以流傳廣遠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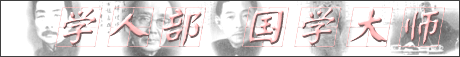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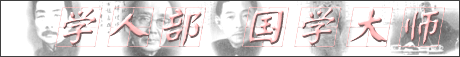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